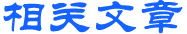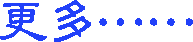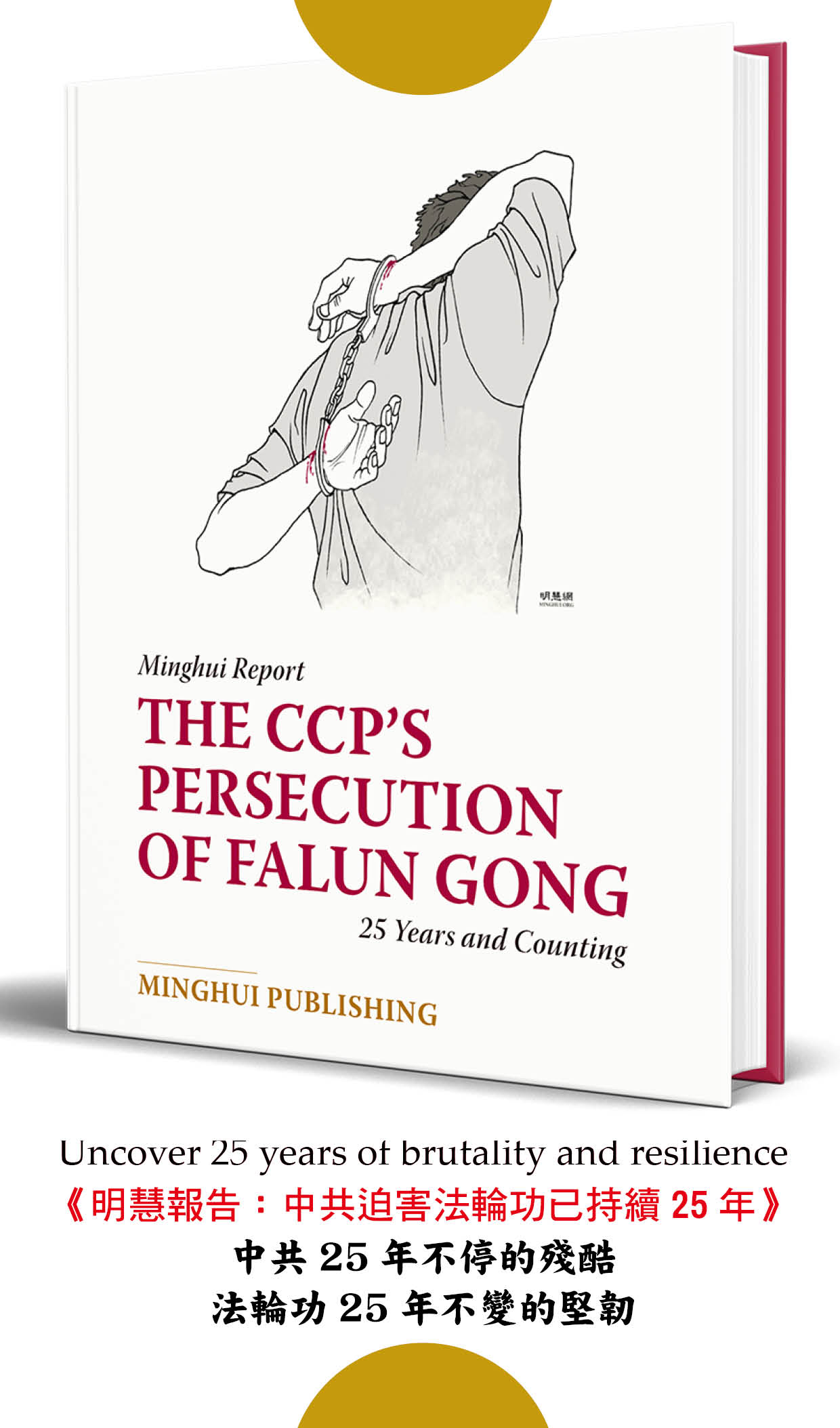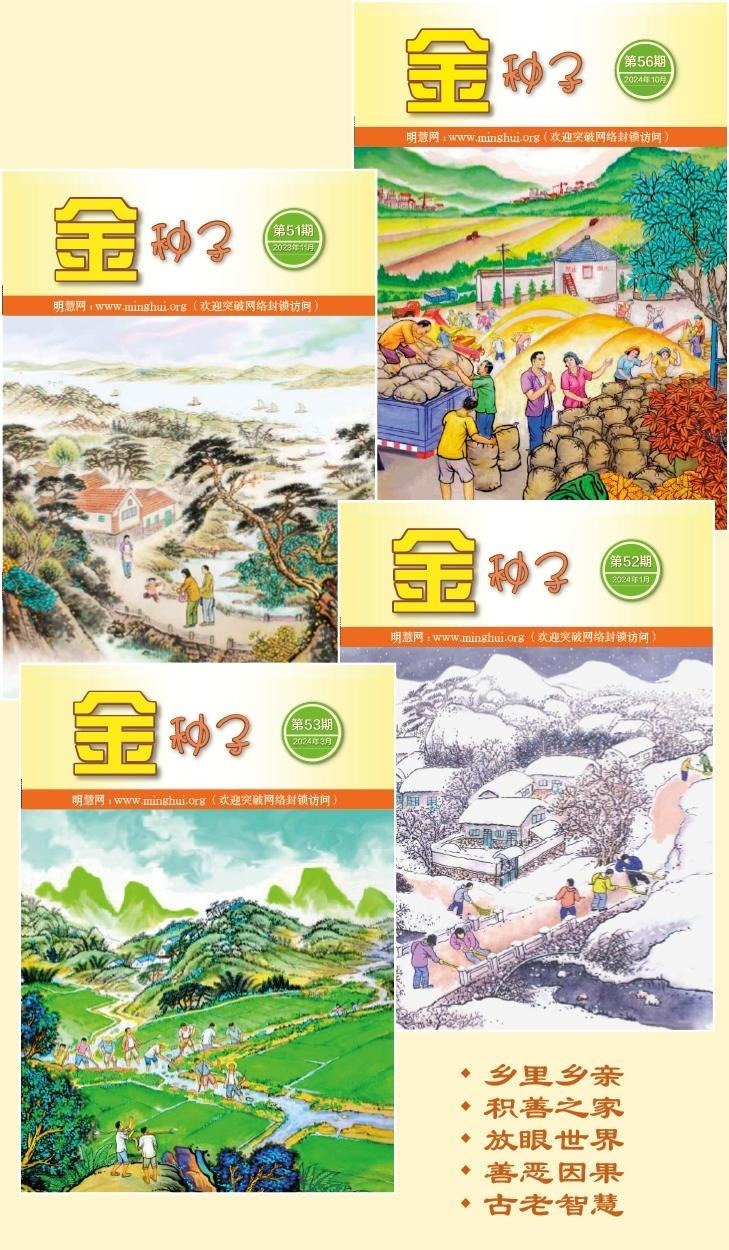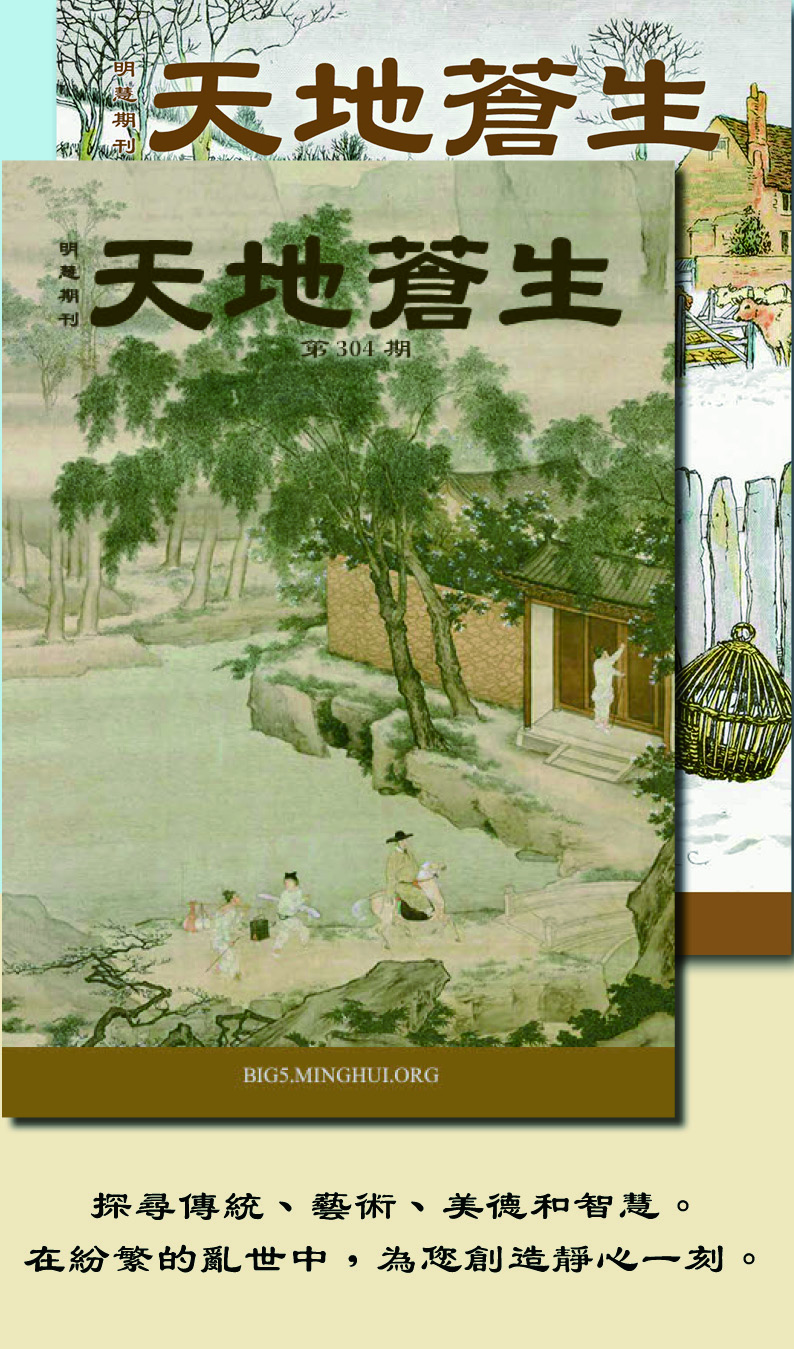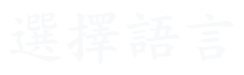一名音乐家在大法中的修炼之路
尊敬的师父!
各位同修好!
我是一名音乐家,自二零二零年开始修炼大法。本次交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我在社会中,以及在修炼群体中的感受
从童年起,我在社会中就感到不自在,这个问题一直伴随着我。有些孩子能在社会圈子中应对自如,能够建立联系、与他人玩耍。而我却不一样。即使是在幼儿园,我的记忆中只有一种令人恐惧的感觉:好象有一股巨大的“人潮”向我涌来,而我却无法理解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父母看到与同龄人相比,我表现的不太“正常”,后来医生诊断出,我有自闭症。这让我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社会。
这种观念就象一块一直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把我与他人隔开。就象有一块玻璃屏障,阻止我与人真正的接触。
每次我想去参加我们国家的大型学法交流会时,总会有某种东西阻止我,这种自闭症的想法也随之浮现。
在我修炼的最初阶段,我加入了天国乐团。
我已经在乐团中有了一个确定的角色,我想这是师父为我的修炼之路安排的一部份。因为我在乐团中已经有了个固定的位置,我不需要再证明“我是否够好”,这让我在修炼群体中感受到了一种归属感。而这种感觉发展得非常迅速。当我开始和乐团一起演奏时,我开始更加理解修炼人,也意识到,我也需要融入到以色列当地的修炼环境中。
但是,要真正走入全国的学法交流会,却还有着各种障碍。第一次我鼓起勇气在全国交流会上分享、倾诉内心时,一位同修站起来,带着很多情绪地说我说得不清楚,他们听不懂。对我来说,这简直就是噩梦成真——我敞开心扉,而他们拒绝了我。后来再次分享时,又发生了一模一样的事情,同一位同修再次站起来说同样的话,这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然而,作为修炼人,因为我开始修善、修忍,那时我也刚开始做学校老师,这让我必须去体会每个人需要什么,尤其是学生。我开始努力培养出宏大的慈悲心,因此我愿意不再只停留在自己的思想里,而是为他人的感受与需要留出更多空间。作为修炼人,其实是很容易理解别人的。
这使我進入了第二个阶段,我发现了一个共同点:如果我身处一个集体中,我就会把所有在这个集体中的人都考虑進去。这意味着,我会百分之百地在场。因为在此之前,是我说,然后听;再说,然后再听,这两件事彼此却是割裂的。现在它们开始联结了。
一位同修的点悟帮助了我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在一位同修家中举行的一天集体精進学法。我们一共四个人,一整天都在学法和交流。学法过程中,一位同修提醒我说话要更清楚一些,对我来说,这就是反馈,也是因为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我用常人的心态去看,这句话本会强烈地触动我的心。但是,因为这发生在专注地学法过程中,而且这句话来自一位我熟悉、让我感觉安心的同修,于是我想到两点:第一,我意识到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有师父法理的指引。与此同时,它也触发了一个长期伴随着我的严重问题,那就是:我在社会中是否真正有自己的位置?当这位同修说出那句话时,它立刻触动了我内心最敏感的地方,但我也在那一刻知道了:我必须突破它!
我开始更加向人敞开自己,因为我理解到自己与宇宙是同一体的。从那一刻起,我开始在读法时开始意识到,我是在面对他人读法,我也是在为他们读。那堵墙开始出现裂缝。
当我开始认真、清晰地读,并且关注整个过程时,我意识到:曾经我说出的每一个字,都把自己内心的不安与不清晰传递给了别人。而现在,当我清晰地读、清晰地说时,一切就变得明朗了。
接着,我意识到,在日常生活中,我其实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我希望在任何一个社交圈里,所有人都能不断地确认“我是好的”,都能不断地向我传达他们把我包容在内了。
这一点让我对《转法轮》第五讲中关于“一心不乱”的内容有了新的体悟——当你和别人相处时,如果脑中装着杂念,那些杂念就可能在你们之间形成一道障碍。
然后我向她(那位提出反馈的同修)分享了我在交流会期间产生的那些感受。那位同修说,确实不可能同时观察所有人,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而且应该保持集中。她建议我每次只关注两三个人,而不是觉得有义务在同一时间关注所有人。这个理解一下子让我轻松了很多。我的感觉就象是:原本密集而不和谐的一团音符,变成了清晰而明亮的大三和弦。
二、我在天国乐团的经历,以及它对我作为一名音乐家的影响
二零二二年九月——波兰“欧洲之路”活动
在二零二二年九月波兰的游行中,我第一次了解了“天国乐团”。我是一名音乐家。当我聆听乐团演奏时,我觉得那是我所听到的,最接近“神韵”的音乐。
二零二三年十月七日 雅典游行
我仍然记得二零二三年十月七日在雅典游行时的感觉。那天早上,我意识到以色列正在发生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我的手机不断地发出异常频繁的警报。但与此同时,我仍然必须在雅典参与救人的活动,并且很好地完成演奏。我知道不应该被外界带动,但我仍然担心家人的情况。
我把自己的感受与乐团成员分享,他们支持我,并帮助我保持冷静与稳定。我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应该保持正念、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到游行中。游行一开始,我之前所有的念头和担忧仿佛从未有过一样,都消失了。我的思维变得相对集中而清晰,我能够专注于当下我所承担的角色。
游行结束后,乐团中的同修向我介绍了由法轮大法修炼者所创作的音乐,我作为一名修大法的音乐家,对音乐创作有了更明确的认识。
二零二四年六月 布拉格游行
在游行前一天的彩排中,我被安排站在队伍侧面,也就是乐队转弯时的轴线位置。也就是说,我站在队伍最前端,负责带领方向,必须认真跟上行進路线以及指挥的带领。
一方面,来了很多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排练;另一方面,我觉得无论在演奏还是行進方面,我们的表现都不太理想。就在这期间,我所在的那一排在转弯时没有转好,我感觉所有的排练象一块巨大的重物压在我头上,随时都要把我压垮。
在我那一排中,有一位乐手无法集中注意力,而我也没能帮助她。最后半小时,小分队负责人让我和她交换位置。本来我应该感到松一口气,但实际上我心里想的是:“她是不是不信任我?” 从那一刻起,即使我觉得自己走得很好,她仍然不断检查我,并告诉我我的步伐、演奏以及整体表现如何、转身如何。我觉得自己做得其实不错,而我旁边那位演奏者表现得还不如我,但她却一直盯着我。这让我感觉负责人把我看成能力不足、不懂事的人。那一刻,我知道我本应该轻松面对,但我感觉身体开始“反抗”:我开始走得不对,音符也吹错了——就好象身体违背了我的意志。我试着调整心态,但脑子里却充满了嫉妒和对负责人的怨气。正因为这些念头,我越走越不好,仿佛也印证了她对我的看法,我感到非常绝望。
排练结束时,我去问她为什么要调换位置,因为我其实有能力承担这个角色,而且对我来说,负责任很重要。我告诉她,我知道自己很生气、不开心,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才影响了我的演奏。我尽量保持“欧洲式的礼貌”,但我确实很难受。我记得,她说她完全理解,并感谢我坦诚分享这些感受,并表示下次会注意。她甚至是带着微笑接受的。
之后我们回到酒店。我记得在晚餐时,因为之前发生的一切,我感觉自己不属于这里,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配得上参加接下来的游行。而之所以会这样,正是因为我内心感受到的那种强烈嫉妒。
我当时心里想:我已经演奏了二十年,并拥有音乐学院的学位,而她只是个初学者;我了解乐团里每种乐器的特点,而她却连一个音都吹不稳,走得也不稳。此外,我曾在旧金山湾区的退伍军人游行中为天国乐团独奏——这意味着作为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乐团,他们知道我是一名非常优秀、能干、认真的音乐家。那为什么他们要把这么重要的角色和责任交给她,而把我放在一个被别人带领的位置上呢?
但随后我意识到,要成为乐团的一名演奏者,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萨克斯演奏者是不够的,还需要承受各种局面的能力,需要处理好自己个人的事情,同时应对乐团的各种挑战,而且还要有很好的修炼状态。我们不仅仅是在演奏音乐——我们实际上就象战士一样,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的部份做好,就象军队里一样。
晚餐后,我回到房间。对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受到了羞辱。但我意识到,我必须接受自己经历的这一切,于是我理解了“谦逊”的意义——不在意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起行动、合作,并信任做出决定的人,这样我们才能作为一个整体行动,让我们的音乐能够救人。
这些经历塑造了我,对我来说是非常宝贵的时刻。我珍惜每一次能够加入乐团游行的机会,因为我其实希望每周都能参与。但我们并不是每周都有排练,所以每一次相聚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时刻。
我把在乐团中学到的经验应用到自己创作的音乐里,即便在与普通人合作时,我也尽量少关注自己的自我,多关注整体的成功。
现在——当我面对任何音乐情境时——我不会只想着自己或者我的“生存”位置。我首先考虑的是:我能做什么最好地帮助身边的人,主动去观察、放眼全局,让情况变得清晰,去服务他人,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份。只有当我们找到彼此连接的方式——我们才能共同成功。当然,这也与我作为音乐家的专业能力不断提升密不可分。
非常感谢师父,也感谢您的倾听。我希望自己作为大法音乐人的道路,在未来会越来越清晰!
(天国乐团成立二十周年修炼交流稿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