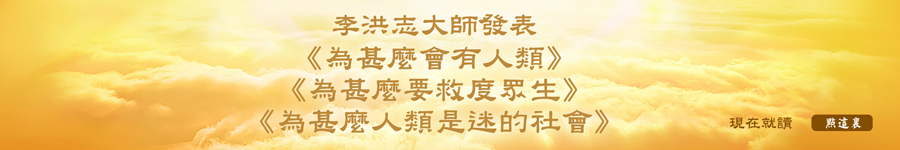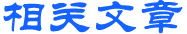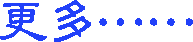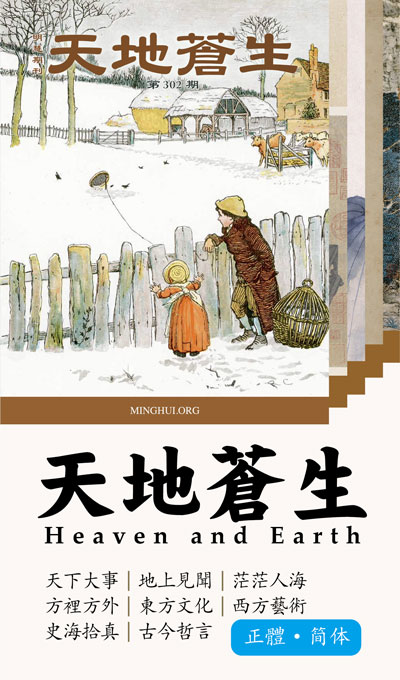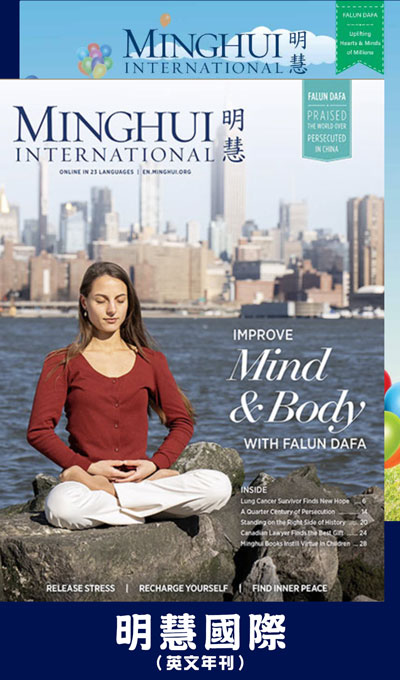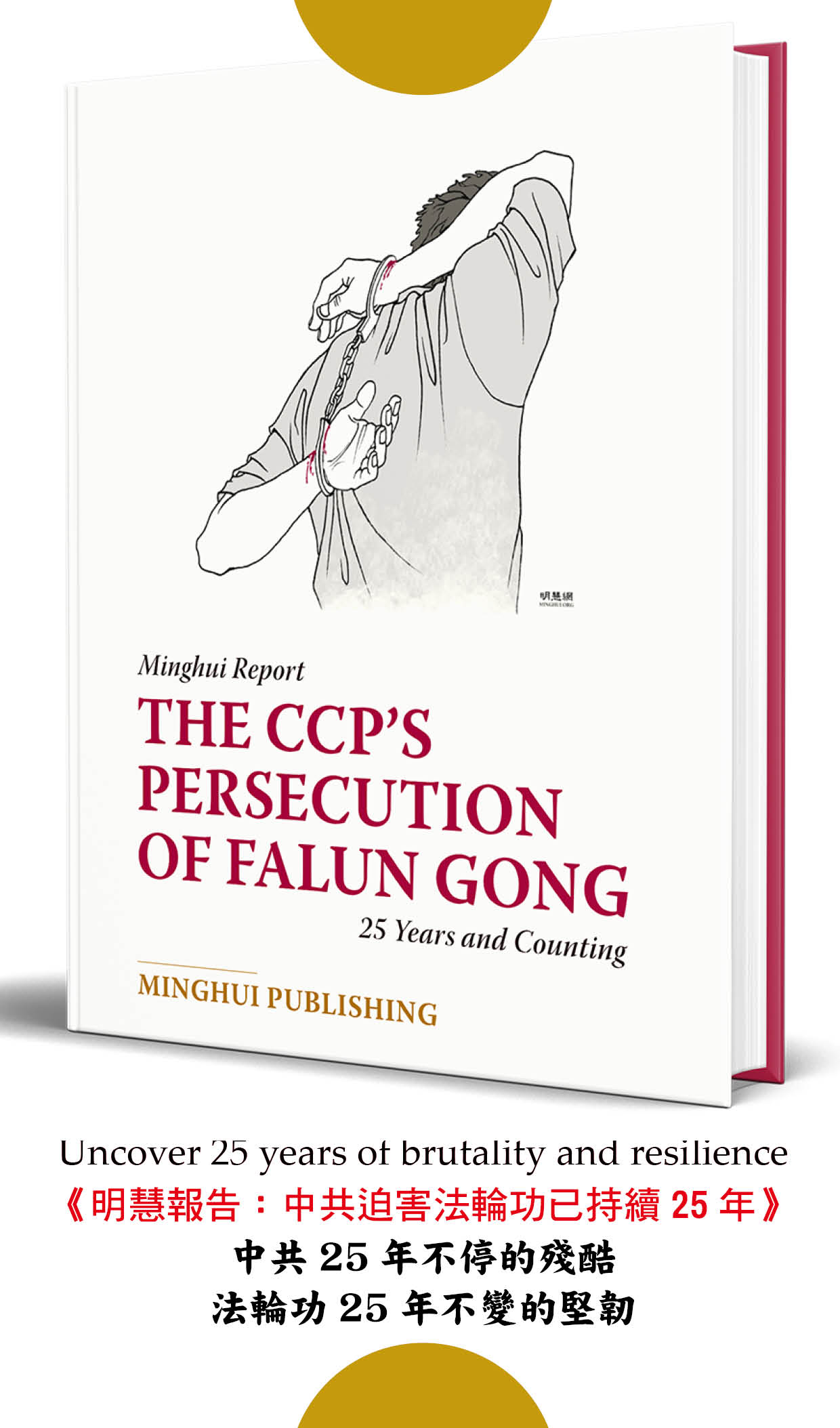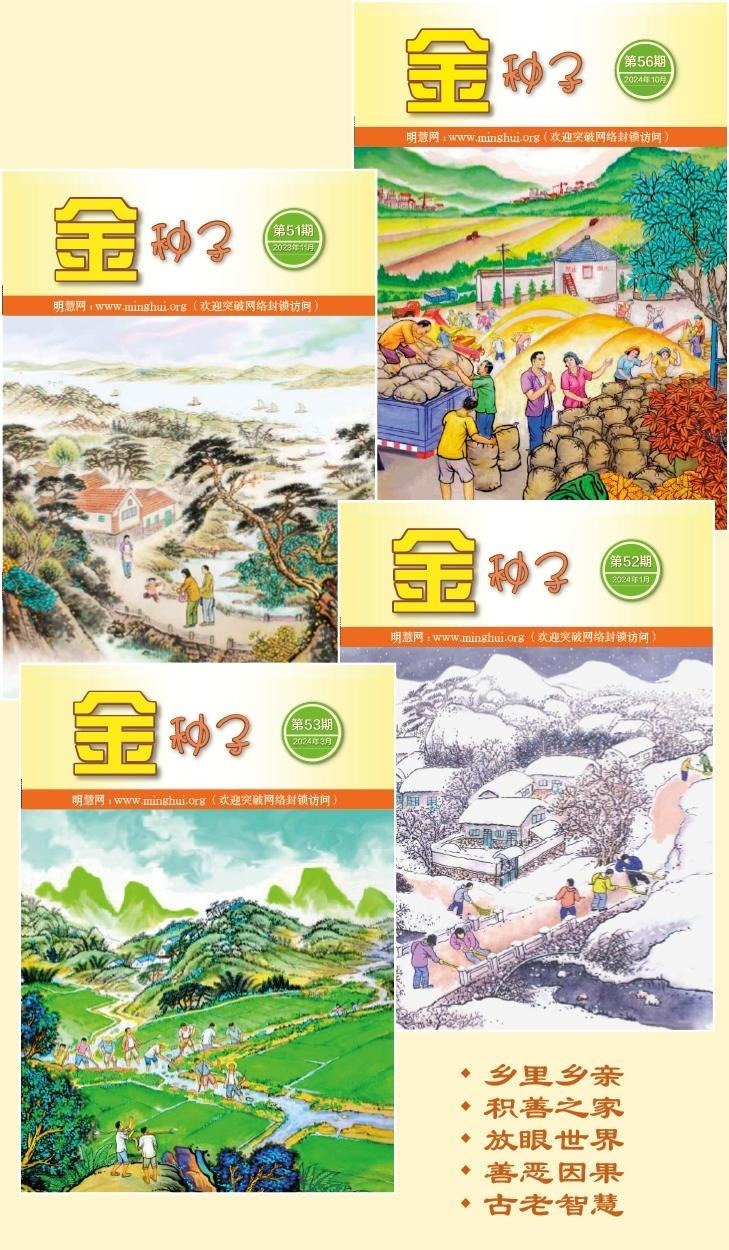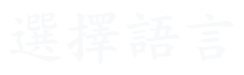三次劳教 五年冤狱 陕西退休教师控告江泽民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三日,罗长云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递《刑事控告状》,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下面是罗长云在《刑事控告状》陈述的主要事实。
一、修大法 是家庭、单位公认的好人
我今年六十一岁多,一名中学英语退休教师。修大法前,我曾患有十多种疾病,药不离身,三十六岁时闪了腰,从此就病魔缠身。腰椎间盘突出,压迫坐骨神经痛,寸步难行;颈椎病、肩周炎,撕裂性疼痛;卵巢囊肿、肛裂,久治不愈,鼻窦炎,咽炎,还有类风湿病,生活几乎不能自理,是有名的药篓子。
类风湿痛的我双手已变形,关节肿大,全身肌肉、骨髓疼痛,手指变形。早晨醒来,全身动不了,叫晨僵,手不能见水、凉的和金属类东西。屋里的拉手全用塑料袋包裹着。没有哪个大夫说能治好的,说是不死的癌症。
两个孩子也得了治不好的病:大女儿一犯病疼的前仰后合,小女儿气喘咳嗽老发烧,经常是左手打吊瓶,右手写作业。丈夫成天不在家,气的我又得了梅花气。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才刚四十岁啊,难道我这辈子就完了吗?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有人送我一本《转法轮》。这本书使我震撼,句句都象金钥匙,解开了我心中一团一团的迷,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吗?书中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高深的道理。人为什么会有病,为什么有苦、有难、有是非,原来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来世是为了返本归真。只有修炼法轮大法,才能懂得如何做个真正的好人。我要修炼,我要返本归真。
修炼法轮大法后,我的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久,所有的病痛不翼而飞,身体健康,心情愉快,全家欢乐。我按照大法真善忍要求自己,道德在提升,心性在升华,工作尽职尽责,受到学生的爱戴。
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的“一人炼功全家受益”是千真万确的,我修炼大法后,两个孩子的病也好了。大法救了我们一家,给了我生活的希望。谁见了都说我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以后,整个人都变了。干工作也有劲儿了,对学生尤其后进生,我把他们当作自己孩子一样,每天放学后留下来,一句一句教他们念,学生家长也很受感动。很多家长要送我东西,都被我婉言谢绝了。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法要求修炼人首先要做一个好人,我做的还不够。学生家长开会,听说罗老师讲几句话,马上热烈鼓掌。掌声几次打断我的话,会后我被一群家长围着,问这问那,象亲人一样。这在修大法以前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有过。
在我被非法劳教关押在陕西省女子劳教所时,我所教过的学生在《本学期最受欢迎的老师》的调查栏目中,都填写我的名字。同时几十位学生家长一同去找刘敬凤校长,强烈要求:要我给他们的孩子们上课!
二零零三年我在单位,六一零不让我上讲台,学校安排我在图书馆,有班主任老师到刘校长那儿强烈要求:“要罗长云给我班带英语课。”这些都证明法轮大法好!领导和同事表示也想炼法轮功。
二、在陕西女子劳教所遭非法劳教迫害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一日,我们全家四人在朋友家吃饭,安康市东城派出所一女警打电话,骗我说是我的学生,从外地回来看我,我刚回到家属院门口,就被两个女警绑架,丈夫说要给我说句话,有穿警服的人说:“过去说个事,一会就回来。”结果一直把我拉到看守所。国保大队李国才给看守所扔了个劳教决定,说:劳教一年零六个月,就走了。劳教决定书没让我看,连一句话都不让我说。
二零零一年过年时,我们炼功、绝食反迫害。元宵节那天,我们八个法轮功学员(五个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被劫持到陕西女子劳教所。劳教所见我们都是老年妇女不收,押送我们的不法之徒拿钱买烟,又给劳教所行贿塞钱,做了一天的“工作”,直到晚上天黑了,硬把我们塞进劳教所。
在劳教所,我们被强迫劳力,超时的干,有时干到晚上,干到天亮早上六点。我们身体受不了,要炼功。
由于我们集体在楼道炼功,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劳教所发动了大规模的迫害,动用了所有的警力,还从二队、三队各调来十个打手,一起来对付我们二十八位手无寸铁的修炼人,而且大多数是五十岁以上的老太婆。他们大打出手。
由于我在集体炼功时是喊动功口令的,我被恶警吼叫着,要抓我。同修们扑在我身上护着我,我被乱棍打懵了,明白过来,我已被铐在铁门外的大教室里,额头肿的,两眼青紫,整个脸变了形。当晚,惊雷在劳教所的上空炸了很长时间,闪放着紫色的彩光。这是对恶人的警示。
梅红英(宝鸡人,六十多岁)牙被打掉,被打得神志不清,第二天,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吴大琼(安康人,二十多岁)当时被打得失去知觉。把我们九人拉出去铐了七天,我被延教五个月,谢小芳(安康人)延教三个月,王秀文(宝鸡县人)延教四个月。然后把我们打散在各队,我和张金兰(西安人,现已被迫害致死)被关到三队。大队指导员是王帆。
 酷刑演示:捆绑 |
在三队,我们受尽了酷刑折磨,因为炼功,我多次被捆绑、暴打,绑在床上、绑在地上。
七月二十八日晚上两点多,号长张艳琴、李利等四人上到我的床上(我在二架睡),把我暴打,李利用脚踩我的脖子,用脏抹布塞我嘴,布条勒我脖子。我的胳膊、腿被吊绑在床上。下铺法轮功学员周亚婷(西安人)喊:“不许打人!放开她!”结果周亚婷也被打、被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的腿肿的不能弯曲,脖子被勒了个血道,路走不了,上厕所蹲不下去。有善良的人见了为我流泪。我去找大队长魏小会,她说:“你腿走不动是你类风湿病又犯了,脖子的伤是你炼功炼的。”同一房间还有法轮功学员王秀珍,(六十多岁安康人,现已被迫害离世),也经常被绑在床上。
 酷刑演示:毒打 |
在不配合点名报数时,我遭到“群殴”,就是被一群人围着拳打脚踢,打倒抓起来,再打。我被打的全身都是伤,胸痛出不了气,去找大队长王帆说理。王帆不但不处理凶手,反而把我双手反背铐在床头上,站不起来,也坐不下去,一动不能动,铐了我二十多个小时。大冬天,晚上很冷,大小便不放。双臂双手失去了知觉。全身痛苦不堪。
后来由于西安法轮功学员张杰晚上炼功,被王帆抓出来,铐在铁门上暴打。大家绝食抗议,又被拉去野蛮灌食,灌的是浓盐水,还不准吐,肠胃受不了,吐了,我的嘴咸了好几天。又把我们铐在队长办公室,王帆亲自拿警棍打了我几十棍,第二天,棍伤正痛时,王帆又打了我几十棍。腰上打的肿了个大包,好长时间下不去。
江泽民对法轮功的“政治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在全国实施,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学马三家的酷刑转化,二零零二年四月,也开始把我们全体集中在一楼强制转化,调来“专干”赵小阳,专门迫害法轮功。赵小阳说:“上边很重视,‘转化’一个奖两万元。打死白打死,是畏罪自杀。”我们二十四小时被强迫洗脑。谁不听,就拉出去暴打。宝鸡学员李翠芳,就说了一句:“你打不进我脑子。”结果被拉出去打得大小便失禁,几乎休克。我和十几个同修被罚站,二十四小时面壁。我们觉得我们修大法无罪,我们不应该承受。我们就被几个恶徒暴打一阵,我被拉出去单独铐在另一个房间。第二天,我的腿肿的好粗,走不了路。这次汉中法轮功学员魏新荣被注射毒药,后来被迫害致死。我们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多数被强制“转化”。我于二零零二年八月被延教五个月后放回。
回家后,心里觉得难过,对不起师父。病又复发。丈夫急的给我按摩,越按病越重。我又开始修炼法轮功。
三、再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四年四月,我正在上班,单位书记打电话让我过去,走到楼口,我就看到国保大队吴星生,我就问他:“你找我干啥?不就是因为我炼法轮功,把身体炼好了,给国家节约了大笔医药费,身体好了工作也有劲了,有啥错?”吴说:“我就找你!”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说我在喊反动口号,就马上打电话,叫来车和几个大汉来抓我,我不走,几个大汉就把我抬上塞进车,就这样我被非法劳教三年。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被劫持到陕西省女子劳教所。劳教所苦力干活迫害,每天要干十八、九个小时,一般都是晚上两点收工,十点收工是极少的。我被迫害成高血压,恶警为了“转化”我,就让劳教所专门给我们做小馒头(三公分宽周长十八公分),相当于平时馒头四分之一大,半碗水煮菜,四个人吃。每个人只给一个小馒头。不让我们上超市买东西,连卫生纸都不让买。
二零零五年冬天,很冷。又把我从三楼打下一楼。李珍为了捞取上级的好处,继续迫害法轮功。我不配合她,她就把我的被子扔到地上,把睡觉的床板揭了,晚上不让我睡觉。还让包夹(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劳教犯人)用剪子扎我。不久,李珍遭报应,被撤职,成为一般小队长,调到南楼(听说李珍现在下肢瘫痪)。二零零六年六月,我被迫害的三级高血压,放回。
四、第三次被非法劳教
二零零七年四月十七日,我给邻居初中孩子《慧声》和《神韵》光碟,他把小册子带到班上,被班主任知道,告诉给校长。第二天,安康汉滨区国保大队吴星生等人就到我办公室,把我抬走,塞到汉滨看守所,非法关押了我一个月。后又给我非法劳教两年(所外执行)。不让我上班,也不发一分钱工资,生活无着落。
五、在陕西省女子监狱冤狱五年
二零零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在广州,因被非法通缉,遭安康市汉滨区国保大队赵思林和东城派出所黄立志协同广州白云派出所恶警非法抓捕,并抄走了我大女儿刚给我的两万多元(其中一万五在卡上,其余是现金)的生活费。
在广州,我被非法关在广州市看守所,后来被关在安康市汉滨区看守所。我被迫害成严重的高血压,有一次量高压二百四十。马佰鹏说:“你随时都有拜拜的可能。”意思就是死。我说,按照《看守所管理条例》第十条,你应放我回家。他说:“保外就医,你又不医治,所以不能放你。”
汉滨区检察院执法人员白××在我无罪的情况下,无视国家法律,非法公诉。汉滨区法院法官张伟浩,伪套《刑法》三百条,给我定罪。结果,在我极度头晕的情况下,不让我亲人知道的情况下秘密庭审,在法庭上张伟浩不停打断我,不让我讲话,非法判了我五年。我上诉,安康市中级法院不审理,非法维持原判。
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大兵端着枪,马佰鹏把我骗去西安,说是去给你医院鉴定,你肯定是三级高血压,放你就有法律依据了。最后医院鉴定确实是三级高血压。马佰鹏靠他“三寸不烂之舌”(他自己说的),把我塞到陕西省女子监狱。陕西省女子监狱接待室的警察说:“三级高血压,直接就是拒收!”恶警杜颖说:“我这儿就专治高血压的。”从此我遭受了最疯狂的迫害,最残酷的折磨。
当天晚上,恶警魏尘来审问,侮辱我,我不想理,她就叫来五、六个打手把我按在地上,说是给我灌药,不锈钢的勺子在我嘴里乱撬。我受不了挣扎着,血流了满地,一卷卫生纸擦血,只剩下手指粗了,勺子被撬成了钮弯的。这些恶徒听魏尘的指挥,要把我吊铐起来,折腾了好大一阵子,衣服裤子都扯破了,后来魏尘说“给打一针”,我被按着打了一针,不一会儿就不省人事了。醒来已经是半夜两点多钟,我被单手吊铐在上床最上杆,我的裤子尿湿了,右手背被铐子顶了个深坑,多少天都起不来。
 酷刑演示:打毒针(注射不明药物) |
从此天天被打被野蛮灌药,一天三次。十几个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在这里,每位二十四小时被两个恶犯看着,想打就关起门来随便打,想骂就挖空心思的骂。上厕所必须听她安排,憋不住时,有人就尿裤子拉裤子,她们又拿你取笑侮辱你、打你。被强行看污蔑大法的书,不看就灌药、打针、罚站,不站就暴打。恶犯大毒枭李爱梅、刘丽红、杀人犯薛芬、盗窃犯邵颖用酷刑折磨我,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我一次实在憋不住了,趁她们不注意,去上厕所,刚去就被几个抓回去暴打。薛芬逼我两腿之间夹一张纸罚站,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打倒在地,薛芬按着我的脚,指挥体重一百四十多斤恶人邵颖用双脚上我腿猛踩我的双膝盖,致使我双腿严重损伤,行走艰难,一年多无法恢复。被迫害的血压高压达二百多。连续九天每天被罚站二十多个小时,每天只让上一次厕所。从早上五点多就让起来,上厕所一次,完了一直站到晚上两点,才能上床,中间都不让上厕所,一天只准上一次,就不敢吃饭,人已瘦的皮包骨。就是早上起来上一次厕所。
我大女儿从宁波专程去西安监狱看我,我身上有伤,不让见,孩子气的哭。
苦力折磨。后来,我被分到七监区,七监区上工时间总比别的监区时间长,经常加班,早上有时六点起床先下车间干活,早餐有时送到车间吃,中午饭时间只有十分钟。苦力迫害,让我做副工,别的副工一人辅助三个机工,而我一人辅助八九个机工,而且还是远距离输送,后来因我血压高,我说干不了,就让我穿肩带,别人可穿一千多提前走,而我要穿三千多还不让走,再使劲也干不完,我手指已经变形伸不直了,每天晚上疼醒来,疼的睡不着觉,手掌、手指长出了几个硬块,(就是现在有时右手中指还伸不直)。血压一高就被强行拉去打针,毒药折磨。
 中共酷刑示意图:注射药物 |
二零一二年,我被强行打毒针,不一会,我感觉天昏地暗,一量血压,低压二百多,高压多少,医务员不敢说,还没大夫,医务员让我躺在病床上,那真是难受至极,差点被致死。它怕外人知道,又把我软禁在医疗所一周。不让给我送任何东西,连裤头都不行。
二零一二年,安康市六一零副主任李文昌和汉滨区六一零头子蒲汉宁到陕西省女子监狱,蒲汉宁说:劳教把你没办法,我只有把你送监狱。
六、回家后 仍遭迫害
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我被放回,我被迫害的神情恍惚,身心遭受了非常大的伤害,身体极度虚弱。视力模糊,手指变形了。而回家面对的是一个破碎的家,老父亲被气死,丈夫被逼离婚,老母亲被迫害的瘫痪在床。十几年来,两个孩子大女儿为了不被骚扰,只得把工作找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小女儿从小学到大学都得不到母亲的照顾,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马上要过年,可是我身无分文,房屋尘土破旧待修。两个孩子和我妹妹给我点钱,才勉强过了个年。
回家后我的自由还被限制。汉滨区东城派出所派专干张××,要求每周到我家一次。张××在出门下楼时摔倒,头上缝了几针,再不来了。
二零一四年八月,我想去看看在外地的女儿,买火车票被限制。马上汉滨六一零张××胁迫单位黄书记、文教局江书记就来我家查阻。我说:二零零五年公通字(三十九)号文件《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没有法轮功,那你们凭什么限制我?凭什么判我五年?张说:“那你告嘛!”
七、亲人遭受迫害
残酷迫害了我十四年,我家无宁日。跟踪、监视居住、窃听电话,我先后七次遭江氏集团非法抄家、八次被绑架、诬陷,非法行政拘留九次,非法刑事拘留二次,非法劳教三次,非法判刑五年,非法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扣发了我被非法关押时的所有工资,十年多不发一分钱生活费,每次我被非法关押,丈夫都会被巨额勒索、敲诈。
绑架、抄我家从来没见什么证件。小女儿问:凭什么来搜查,有搜查证吗?汉滨国保大队赵思林回答:“难道你不认识我?”那意思是他的脸就是。十四年来,据孩子的父亲说,他被敲诈勒索十几万。还非法抄走了我家两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和大法书、录像带、DVD光碟机两台、手机数部、mp3六、七个、电子书七、八个等和大量的现金和物品。丈夫因受不了这无休止的巨额敲诈勒索,二零零六年与我离了婚。
二零零八年,我被绑架后,国保大队吴星生又闯去我老娘家审问我母亲。八十岁的老母,以前严重高血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病全好了。在江泽民铺天盖地邪恶的迫害下,实在经受不了亲生女儿遭受这无辜的残酷迫害,被惊吓懵了,大小便失禁,四肢不灵,从此瘫痪在床至今。给我家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给孩子的心灵一直留下无法忘却的痛苦记忆;给亲朋好友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6/10/8/15945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