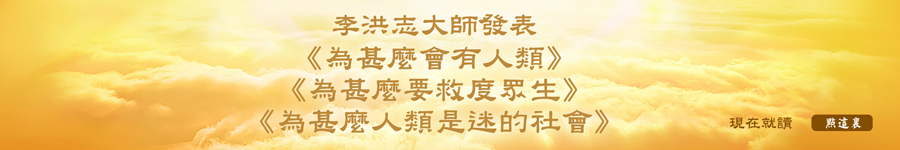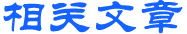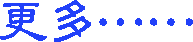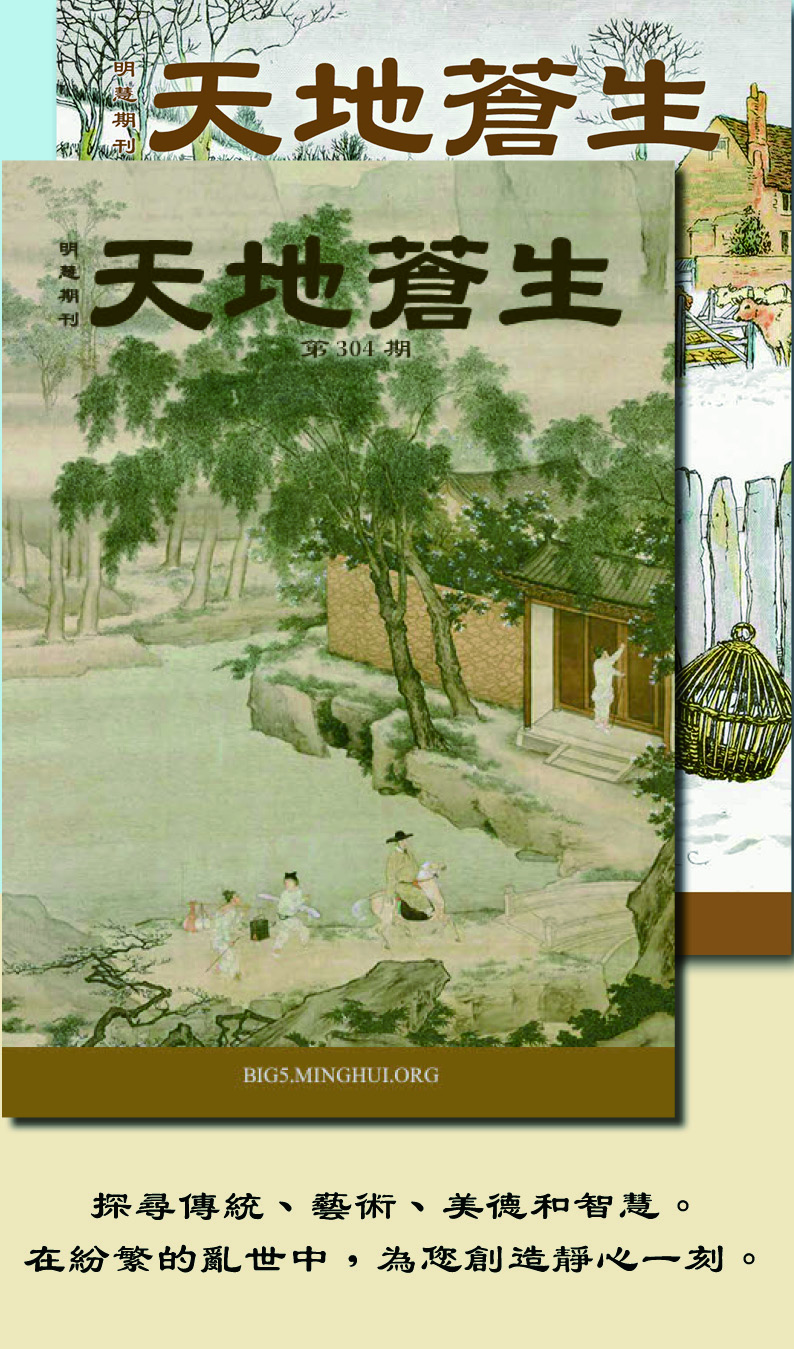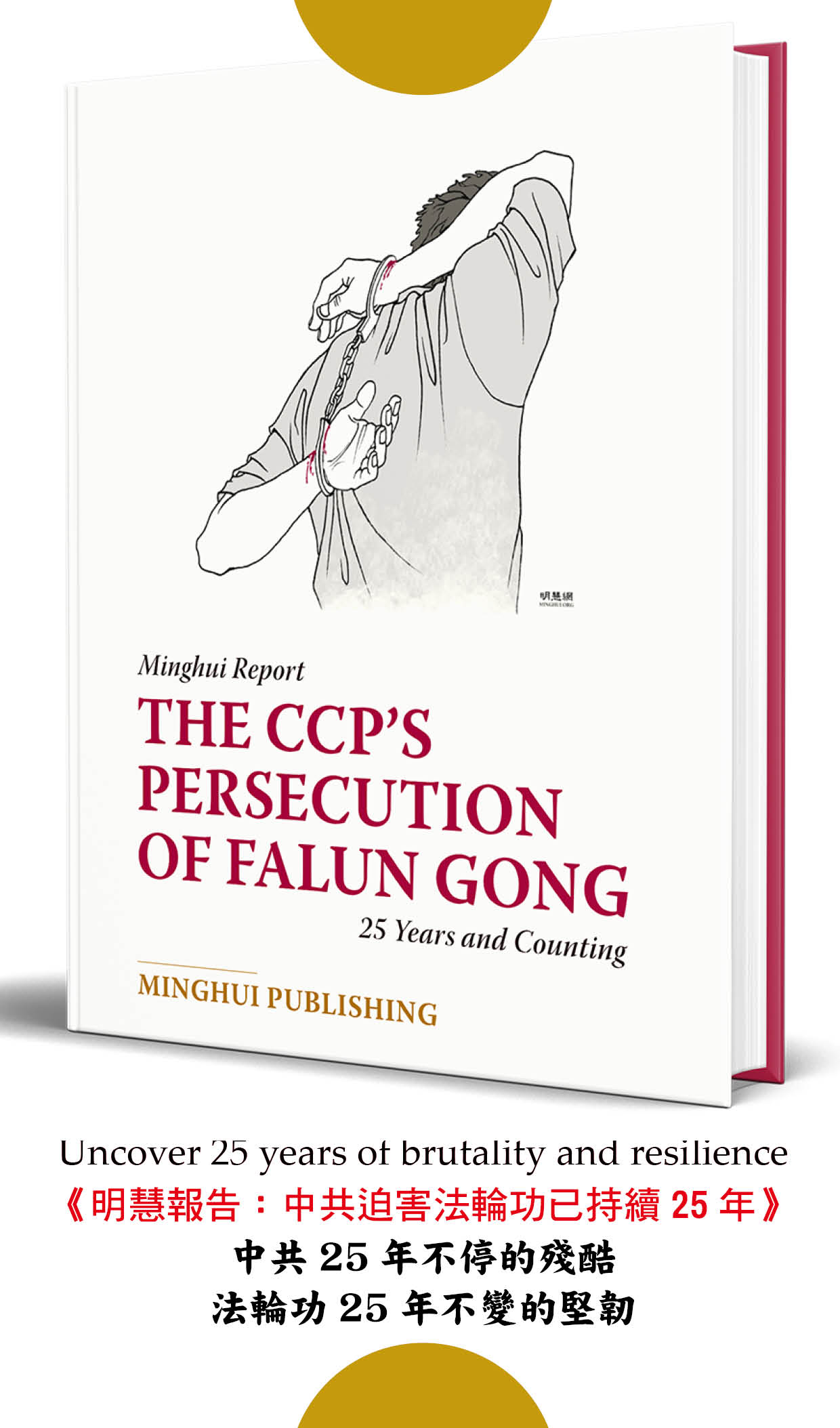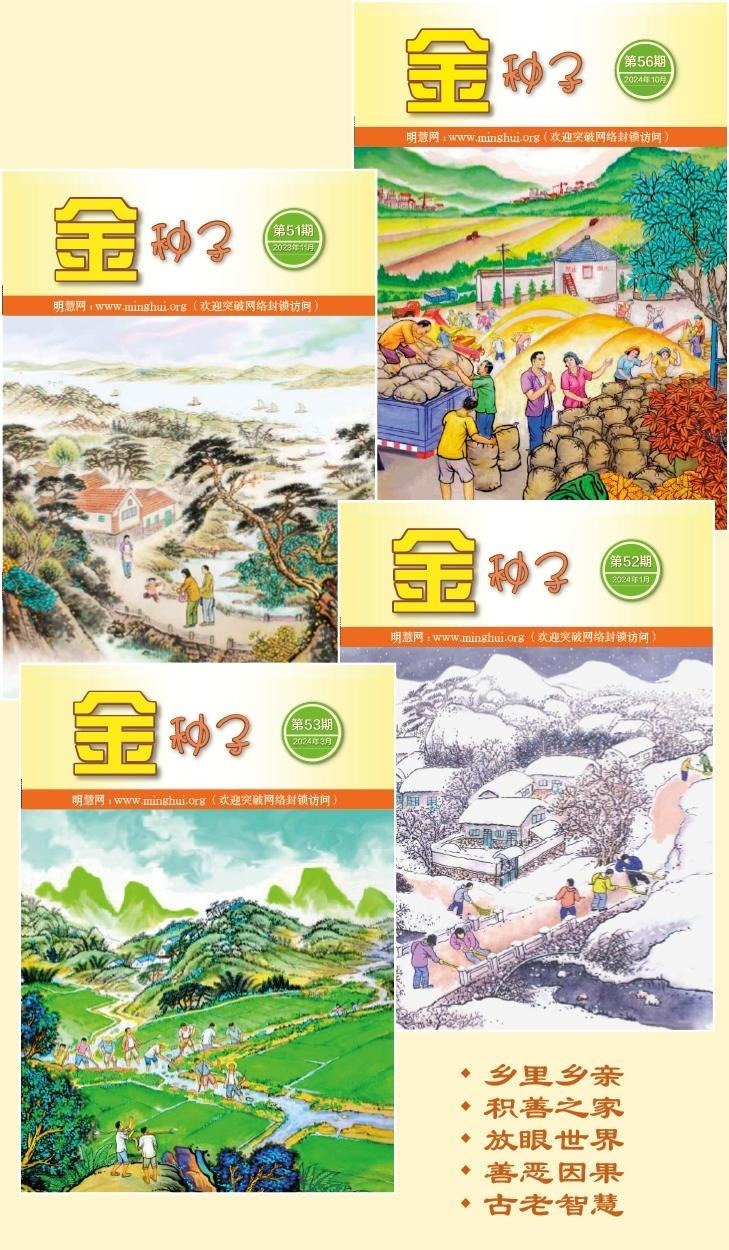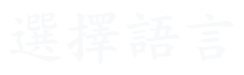被迫害家破人亡 卜庆金夫妇起诉江泽民
在一九九九年七二零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给卜庆金的家庭造成了家破人亡、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的悲惨遭遇,夫妇二人一次次被关入黑监狱,其岳父含冤离世,儿媳遭受不了一次次的骚扰,带着女儿离婚。
以下是卜庆金叙述一家人遭迫害的片断:
夫妻被关洗脑班 老岳父含冤离世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我在结束了一天井场上的辛苦劳作后,正准备下班回家,王炼杰指使蔡云山带领一帮打手,到防砂队又一次将我绑架到作业二大队黑监狱关押。关押几天后又转入采油厂黑监狱长期非法关押,王炼杰任监狱头。同时,我的妻子付传美也同样一起被绑架到孤东培训学校的黑监狱中遭受折磨,付玉新任监狱头。
房子的窗子顶部只留一个小孔,并用粗钢筋焊上,下部全部封死,铁门上焊有小铁门,用作送饭口又是观察孔,里边没有暖气,只有一根细管子,所谓的暖管,但也不热,根本不是取暖。在哪儿一关就是近五个月,当时去的时候天还不是太冷,穿的衣服很少。一冬天挨饿受冻,受尽了折磨,那里的看管人员还经常对我拳打脚踢,受尽了凌辱,二零零一年春天,王炼杰又将我押送到东营教育学院洗脑班洗脑、仙河社区洗脑班以及济南监狱在胜利宾馆组织的洗脑班进行多次强行洗脑。随后,又回到了孤东黑监狱进行关押,直到二零零一年四月底才得以回家。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份开始,在我夫妻被孤东采油厂惠成龙、王炼杰非法关押的过程中,我七十六岁的岳父傅忠兴见此情景,就来到仙河镇女儿家给我们照看孩子。当时,傅忠兴老人的大儿子也因修炼法轮功在山东省第二劳教所遭受三年的劳教,二儿媳妇同时也在济南被非法关押,老人家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外孙和十三、十五岁的两个孙女一起生活,每天不仅要照顾好三个孩子,还要带着孩子们到处寻找被单位绑架的女儿和女婿。同时,还在承受着王炼杰等恶人一次又一次给他们带来的逼迫、恐吓,以及在生活、修炼等各个方面给他们施加的压力和骚扰,多次逼迫我岳父傅忠兴离开仙河镇,老人家非常健壮的身体,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被他们迫害的起不了床。我夫妻二人被放回家不久,老人家已经被他们迫害的骨瘦如柴,与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我的岳父傅忠兴被王炼杰一伙迫害的含冤离世。
洗脑班、劳教所的酷刑折磨
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八日,我又被滨海公安局警察绑架。因妻子付传美回老家去给我的母亲过生日,他们没抓到她,李光明、蔡云山等一帮人又连夜驱车赶到我老家泗水,全家翻了个遍,没有找到付传美,而后就对我八十岁高龄的老母亲进行威胁、恐吓,最后把老人家折腾的昏死过去,他们不仅不去救人,而是一个个灰溜溜的逃窜了,在离开时,他们还预谋设圈套,说给八百元把老人拉来给孩子做饭,作为诱饵来要挟、引诱付传美,可是八十的老人怎么还能照顾孙子啊,所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又到我的所有亲戚家全部翻了个遍。
我再一次被关进了孤东黑监狱内,我为了抵制迫害,进行绝食抗议,孤东一帮恶棍十几人,把我绑在铁椅子上腰部用方木棍压紧,两端上锁,脚腕部上锁锁住,椅子上边绑上长棍子,把我的两手拽直,用手铐铐住捆在棍子的两端,给我进行鼻子插管,野蛮灌食,插的鲜血直流,至今吃饭不注意就进了鼻腔,难受至极,并且他们还给我打不明药物。灌食十多天后他们又把我送到所谓的山东省法制教育中心进行继续洗脑和灌食。在那里,洗脑班是和山东省第二劳教所联合迫害的,我被送到最邪恶的十二大队,每天由孤东恶人刘凯与邢世忠强制押送我到劳教所所属的医院去野蛮灌食,他们二人把我按在椅子上,将我的两臂别在椅子的底部,在两边一拽,疼得就象胳膊断了一样搅心。灌完食后他们就拉着我送到劳教所进行迫害。
劳教所更是残暴,初春的天气还是很冷的,大队长张波领着一帮恶人往我头上浇凉水,棉袄全部给浇透,逼迫那些转化者轮班折腾,孔铁柱、华明亮拿着带楞的枣木棍猛砸我的头部,砸到了华明亮一举棍子我的神经都往出蹦的程度,梁兆贞用他粗壮的大巴掌打我的脸,我本来是很消瘦的脸颊,被梁兆贞打得变成了像茄子色的黑圆球,副大队长张波看到我的脸被打成那个样子,赶快说:“你赶紧把脸转回去,我不敢看,我害怕”。我单位的所谓陪教邢世忠,看着我的脸却找不到我,已认不出我了。后来他们不敢再送我回洗脑班,就给我热敷,三天后消肿了,他们又送我回洗脑班。
李光明一伙没有找到付传美,很沮丧的回到单位,在到处打听她的行踪,付传美听到我被迫害得不成样子,就到劳教所给我送衣物,接着就被单位看管我的人留下,在洗脑班一同被洗脑。当付传美看到我被打成了这样,就对洗脑班提出了抗议,他们只好拉着我去医院做CT,当然他们不会查出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都得听从中共的,最后也只好不了了之,可是那些迫害我的凶犯不长时间都被劳教所提前释放回家了。
在洗脑班迫害一个多月后,孤东邪恶人员又采用找熟人、请客送礼拉关系的手段,将我夫妻二人一同送入劳教所执行为期三年的劳教。在劳教所里我受尽了各种凌辱和酷刑折磨:熬鹰、上大挂、冻刑、饿刑、罚站、长期面壁、凳子磨屁股、凳子砸胸脯、床头铐、筷子砸手指、鞋底砸手背、跺脚趾、光屁股长时间在地板上冰、长时间(三十多小时)憋尿,不让解大小便,棍子砸头、打耳光、掏心锤、鞋底砍脖子、超强度的劳动、大管抽血等等无所不用其极。
酷刑熬鹰
在刚刚进入劳教所的一个多月里,被迫害的大法学员只要不转化是不会让睡觉的,长时间坐在小木凳子上,凳子的腿是活的,来回晃悠,并且在凳子面上有的楔有钉子,有时是沾上的硬干胶,用凳子专门磨我屁股,把手放在膝盖上不能动,动就会被打,整天让一帮一帮的所谓转化着,连续不停的灌输邪悟的东西,每天分几帮人熬我,我在一班共二十八人,二十七人轮换着熬我,当然,也有很多帮助我的,但只是暗中提供方便。长期的煎熬使我心神不宁。并且,不长时间就把屁股磨破了,血肉和屁股粘在一起,大小便非常的困难,拽开肉皮的痛苦真是撕心裂肺啊,为了隔开衣服,就用卫生纸粘上,卫生纸干在屁股上再坐凳子,也是一样的疼痛。不让我合眼皮,一合眼马上就是一顿毒打,或是冷水浇头(在冬天),或是竹筷子砸手指,皮鞋踩脚趾,打脸脚踢那是家常便饭。当时熬的我掏兜竟掏进别人的衣袋里,往膝盖上放手能放在别人的膝盖上,走路时身体向左侧倾斜有七、八度,熬的不知东西南北,不仅如此,还有人灌输诬蔑大法、邪悟的理论。
上大挂
恶警把我关在严管室里,门窗全部封死,走廊里的电视开的震耳欲聋,找了五、六个邪悟的彪形大汉,由王军坐在椅子上指挥,首先用烂布把我的嘴椎结实,再用宽胶带在烂布的外面封上粘结实。初春的天气还很冷,给我扒掉棉衣,打开外面的窗子,手腕上铐上手铐,吊起来挂在窗子外面,脚尖似乎沾地又不沾地,腰正好担在窗台的棱上,再由五六个人象恶狼一样的扑来,有掏胸的、有掏肌肉的,又在胯骨底边向外抠大筋的,有挠痒的,手段残忍毒辣又下流。不一会就折腾晕了,等你清醒了又是一阵子。最后,我感到天晕目眩,五脏六腑都要从口中吐出来了,顿时口中堵的所有脏物全部吐了出来,我也清醒了许多。四月初苍蝇还不多见,可是此时苍蝇象流水一样从窗子里涌进来,马上两间屋的房顶变成了黑的。
砸手指
他们为了不让我睡觉,最后把我的手砸肿砸烂,冬天的时候用水一洗,手指的各个关节处全部裂成了大口子,裂的很深,甚至裂到骨头,再用筷子一砸疼得钻心,疼痛难忍。有一次,他们直接把我砸休克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有时他们狠毒的把我的手按在桌子上用皮鞋底拍,不一会十个手指甲底部全渗满了血,很长时间才能退去。
凳子砸胸
在所谓的五班时,田本印是副班长,他负责包夹我,别人出去吃饭,田本印在那儿看着我,他经常迫害我,有一次田本印用凳子猛砸我的胸部,前胸砸了后胸砸,砸了几十下子,直到我爬不起来他才住手。
冰刑
我在睡觉的时候,把胳膊放在枕边上,恶警就把我拖出去,大冬天在冰冷的地板上一冻就是几个小时,冻的不能动了,恶警再找人拖回来,这样的事情经常出现。
我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罄竹难书,进劳教所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把我迫害的不能行走、不能说话,上厕所都要靠人照顾。经济南医院认定,说我以后已成了一个废人,再也不能走路了,不能说话了。就是那样,劳教所的恶警也没有一刻停止对我的残酷迫害。劳教三年的期限又延期了三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