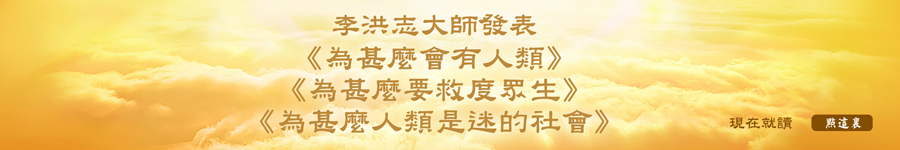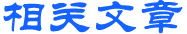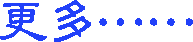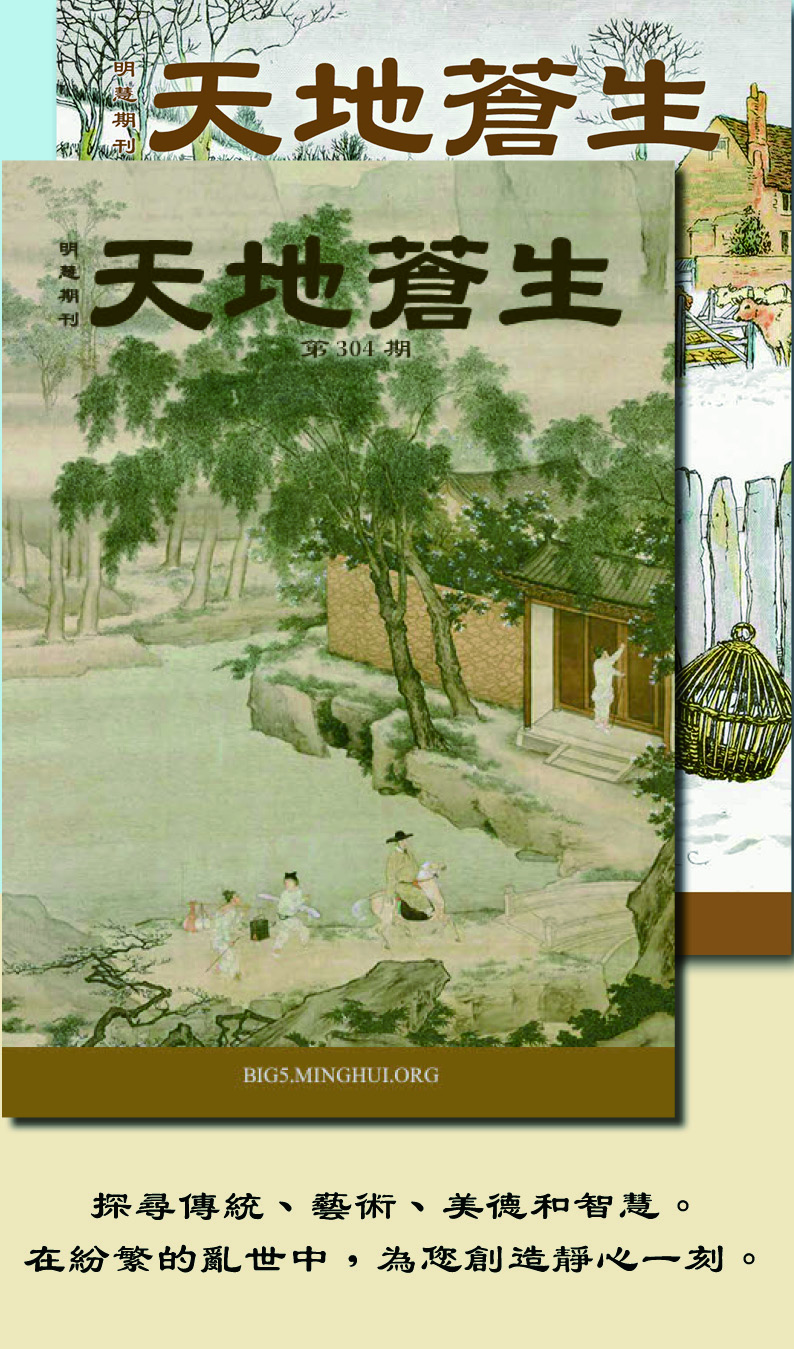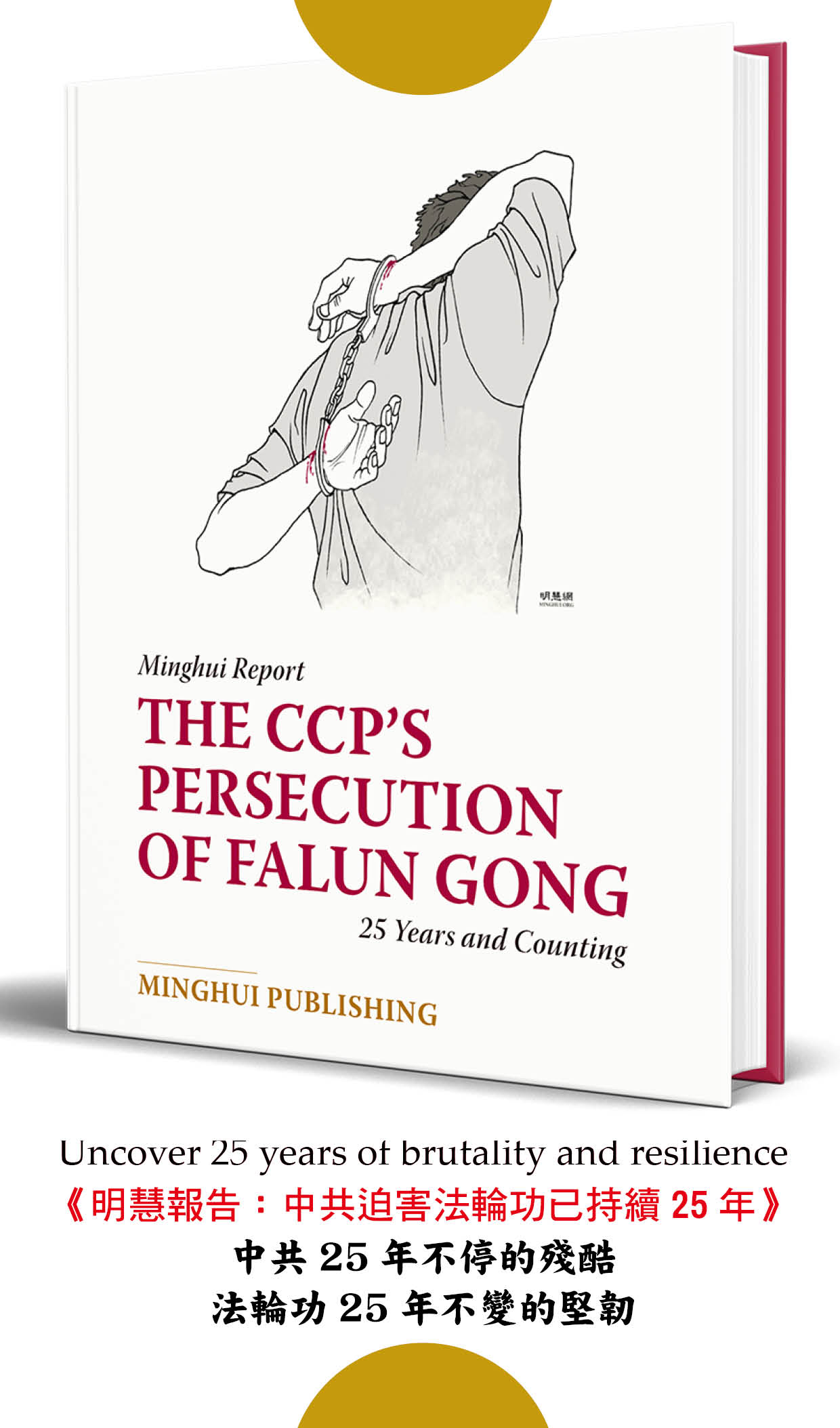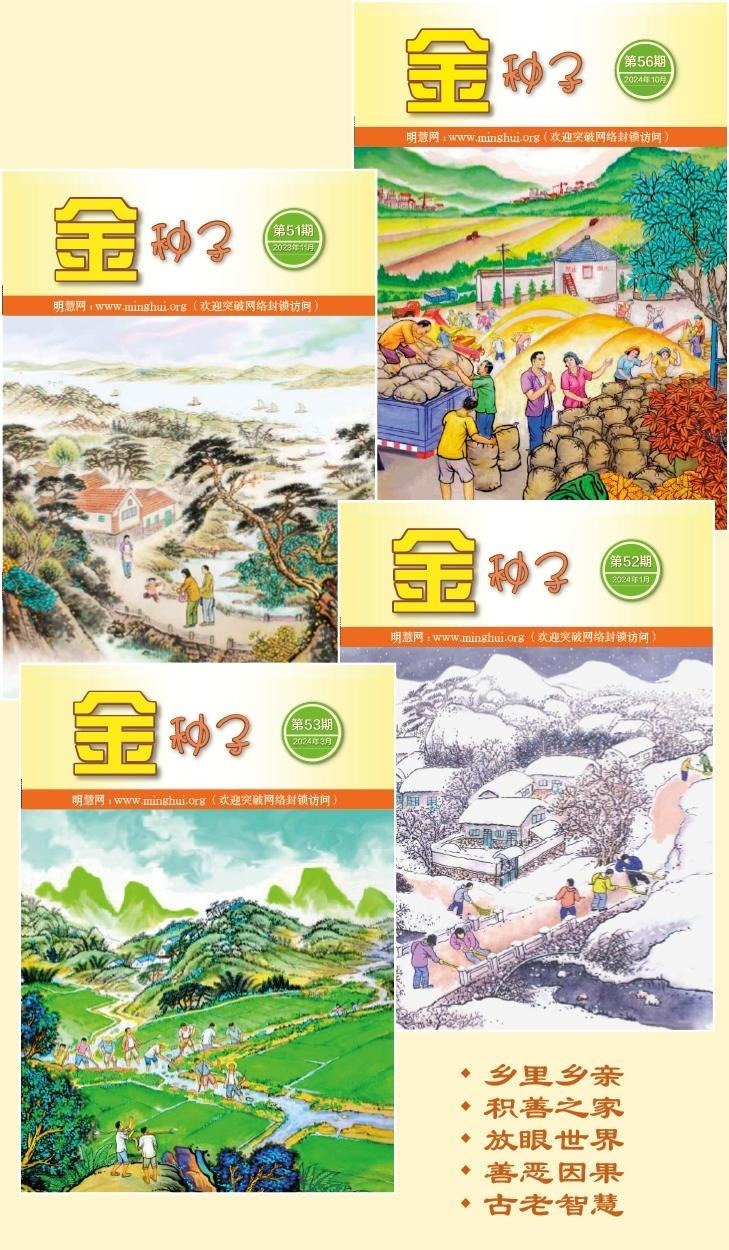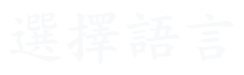到拘留所看望亲属被扣留 吉林妇女遭酷刑与侮辱
法轮功学员程丽静女士遭到酷刑折磨与侮辱:扇嘴巴、开飞机、老虎凳、用针扎、来月经被水浇、被扒裤子……
 酷刑示意图:老虎凳 |
中共不法警察对这些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虽然已经过去了四个多月,但是酷刑折磨留下的伤痕仍在。程丽静的右手手腕现在有时还一阵一阵地疼痛,胳膊有时也一阵一阵地疼痛,不能正常生活;刘桂红依然身体很弱,乳房还会出血……
一、程丽静自述被绑架、迫害的遭遇
我叫程丽静,2013年6月5日那天,我去农安拘留所看亲属,10点多钟到那里,在车里等候,不一会就过来二三十警察,给车包围住,为首的是农安国保大队队长唐克和古城派出所所有警察,强行把我绑架塞进警车。古城派出所任楠开车,我旁边坐着一个左脸有黑痣的警察,任楠上车就破口大骂一些脏话,还说两天中午没睡觉。
到了古城派出所,十多分钟后,有一个警察把我叫到了另一个屋(一楼右拐,靠右边第二个屋,里面有电脑)。这时一个警察(男,大约三十多岁,单眼皮,身材胖)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看亲属。并问我的名字,我没有回答,他就出去了。这时,又进来一个警察(男,左脸有一个黑痣,三十左右,中等身材,皮肤白)动手要扒我裤子、耍流氓,我大声喊:“警察打人啦!警察打人啦!”这时进来七、八个警察,其中有唐克,问我说没说什么,欲施流氓的警察说:“没说”。
唐克让其他警察拿来手铐,开始给我上背铐。并自我介绍说:“我叫唐克,国保大队的,在明慧网上有名,法轮功学员于长丽就是我打死的。”然后开始非法审问我。我依旧拒绝回答。唐克就和七、八个警察把我按在地上,恶毒地在背后往上掰我胳膊,反推我胳膊直到和我头平齐。这样折磨完我,使我浑身一身汗,脸上都是大汗珠子,我疼得昏死过去,不知谁拿毛巾给我擦脸上的汗。
在折磨行恶期间,警察在不告知我的情况下,扎了我的手指和耳朵进行采血,我看到桌上有一个小盒写着采血字样。他们还继续向上提拽我的手铐,迫使两只胳膊从后背往上一直被提到头上与头垂直(古城派出称这种酷刑为“开飞机”),这种酷刑在这个屋里给我连用了两次。
后来古城派出所的警察把我弄到餐厅里,开始轮番扇嘴巴,把我的脸打的肿胀,打完后逼我挨着窗口,在下面坐在地上,拿来一水舀从水龙头接的凉水,照脑袋上垂直就倒下来,把我浇的浑身湿透,接着他们又拿来电风扇吹凉风,我被吹得浑身哆嗦直打冷战。一个二十多岁的圆脸男警察用脚使劲碾、踩我的脚,把我疼得几乎昏过去,接着继续打我耳光。
这时国保大队组长吕明选和周大海来了,吕说:“咱们互相尊重”,问我姓名、住址,见不回答,吕明选上来就打了我一个嘴巴,还叫嚣要刑拘我。周大海骂骂咧咧地一脚踹在了我的额头上,脑袋磕在墙上。见我不说就走了。
中午的时候,不知是谁在餐厅通过窗户朝我撇来一根打折的木棍,打到了对面的墙上。
还有一个叫王猛的年轻警察打我嘴巴,这时接班的警察来接班了,他们还要继续打我,王猛说:打一天都要打死了,别打了。这帮所谓的警察在走廊里说着不堪入耳的脏话。
晚上把我和其他四名法轮功学员关在一个屋里,将近七十岁的老同修被铐在老虎凳上,我的右手被铐在左边老虎凳腿上一宿。值班的黑体恤说:让你们不说,等明天唐大队来,让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
从我被绑架到派出所,我就一直要求上厕所,警察一直不允许,直到第二天我才利用验尿的机会上的厕所。
6月6日早,八点半警察上班后,“白体恤”、“黑体恤”让我们都在地上蹲着:手铐在老虎凳上铐着。一个穿白T恤衫的男的用针扎我的胳膊六、七次,无明显外伤,但却非常疼痛。一个二十来岁的小眼睛女警察往外掰我铐在老虎凳上的右手中指。
又把我整到餐厅,开始往我脑袋上浇凉水,打开电风扇吹凉风冻我,冻得我上牙打下牙。这时又被逼迫跟着小眼睛女警察上厕所验尿,并且不让我关厕所门。我来了月经。我请女警察帮我买卫生巾,女警察说:“不给你买,挺着吧!”从厕所回来之后,我先在瓷砖地上坐着,然后又强迫我蹲着,连水带血淌了一地。又强制我趴在地上,继续“开飞机”,穿黑体恤衫的年轻男警察不停地打我嘴巴,穿白T恤的男警察用脚踢我的脸,还把穿的鞋脱下来,用鞋打我的脸。他俩又把我在地上拖拽到门口。让打更的老头把地上的血水拖干净了。我又被迫开了两次“飞机”。他们在折磨我的过程中,外套不知何时被扒掉了,贴身的T恤被撕碎了,多处皮肤都裸露在外。
唐克又过来说:“是不是没说?!”就打我耳光,并说:找绳子上二楼吊起来。他就出去了。长春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一个人(四十来岁,一米七五左右,挺胖的,穿砖红色格衬衣,平头,四方脸,眼睛小,夹一个公文包)进来了,我浑身被浇湿坐在地上,双手被反铐在身后,费力去捡外套,他看见了伪善地让我坐在椅子上,打开一只手铐,让我活动活动。当时我的两只手,肿的像馒头一样,手腕都被勒破了。我当时头发被浇透了,被薅拽的乱七八糟。我伸手去拢头发,他说:“你给头发拢拢。”我向他要来手纸,擦擦鼻涕。这时又进来一个古城派出所的警察,看我头发梳起来了,上来就使劲拽我头发一把,并说:“还梳梳头!”610那个人便开始问我家庭住址,并问我认不认识谁,回答说不认识。就又给我在前边铐上手铐。又问我学几年了,还说6月3日抓孙燕霞他们是长春统一行动,抓的谁都有名字。看我不说什么,就走了。
任楠把我弄到一个屋子照相,正、左、右脸都照了。一警察把我又带回有老虎凳的那屋,这时吕明选来了,开始骂我“不懂人语,死猪不怕开水烫”,还打了我一个耳光。
6日下午三点多,我被弄到拘留所非法拘留十五天。我的整个脸都被打变形了,衣服被撕碎了……
 |
在拘留所期间,吕明选和周大海,还有一个国保大队年轻的警察曾三次(最后一次是吕明选自己一个人)到拘留所恐吓威胁,要提审、加期、劳教等等,吕明选逼问出我的姓名后,骂道:以前我就要抓你,我没抓到!然后就开始辱骂我。周大海也骂着不堪入耳的话。
从六月五日上午十点遭到绑架,一直到第二天下午三点劫持到五公里拘留所,一共三十个小时,水饭不给,不让上厕所,晚上不让睡觉。
回到家中,收拾家务时间稍微一长,我手腕都疼的干不动,拎半桶水都费劲。现在右手手腕有时还一阵一阵地疼痛,胳膊有时也一阵一阵地疼痛,不能过正常生活,给我和家人带来严重伤害。
二、刘桂红自述被迫害过程
六月五日,我和亲友正在农安五公里拘留所门外的车上,突然一帮警察就把车团团围住,把车上的人撕扯着就往外面的警车拽,我和程丽静被劫持到一个警车上,司机是古城派出所的任楠,还有一个是古城派出所的警察(男,左脸有一个黑痣,三十左右,中等身材,皮肤白。就是他后来要扒程丽静裤子)。
刚上车,任楠就骂,说什么“大晌午头子,不让睡觉,都两天了,昨天就没睡,今天你们又忒瑟来了!(带脏话)”车刚开一小会,我心脏就特别难受,就要吐。我就想上包里找塑料袋。旁边坐着的脸上带痣警察看见就特别横地说:“不能动!不能动!”程丽静说她要吐,就要帮找纸。他一把就把包抢过去了,并说:“看你兜里有啥?!”看后侮辱说:“这都啥破玩意啊。吐就往这兜(指我的挎包)里吐吧。”
到了农安县古城派出所,我身上就突突,站不住。是程丽静扶着我进去的。病变的乳房疮口,不知何时被弄的流脓、流血不止。到了古城派出所,我已痛得跪伏在地上,头顶着地、蹶在那里。程丽静让警察别动我,说我有病,是乳腺癌。程丽静想上前把我扶起来,警察指着她说:“去!不用你管!上那边去!”后来一个警察踹我的屁股一脚,并说:“她咋回事啊。”还说:“就这样还出来呢,我们就不怕这个,死了最好,直接就送火葬场炼了,这离火葬场还近。”还有个警察侮辱我说:“她咂咂(指乳房头)疼,你(指男警察)周开看看是真的、是假的。”等许多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
就这样一直从上午十点左右到晚上十点前,我疼得一直头顶着地、或顶着墙。警察对我的病情不闻不问,反而一会就有一个警察到那踢我一脚,说看我死没死呢。
期间,我想去厕所,几次都没有站起来。崔贵贤几次向警察要求扶我站起来均遭警察拒绝。一名男恶警说:就给你二十秒时间,再站不起来就往裤子里尿。我硬支撑着站了起来,但身不由己就快摔倒的时候被崔桂贤扶住,我脱下鞋子光着脚继续朝厕所方向走去,结果因为身体虚弱连门槛都没有迈过去。有警察一看说:就你这样,厕所里还有台阶,你能上去吗?崔桂贤说:你们给拿点东西接尿吧。崔桂贤帮我接尿。弄到地上的尿,恶警让崔桂贤用衣服擦干净,崔桂贤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尿擦干净了。当时屋里共有四个警察:一个男警察在窗口站着;两个男警察在门口站着;一个小眼睛女警察(二十多岁。当时是长头发,二十多天后剪成短发了)
大概晚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我跟小眼睛女警察说:“我要跟你们领导说话,我是得的乳腺癌,我这种情况,你们是不是应该放我回家。”她又跟同被关在一起的人(屋里有9个人)说:“你们都听着,我这种情况,他们还不放我回家,我要是死在这里,你们给我证个明。”过了半天,进来大约三、四个警察,我跟离我最近的那个男警察说:“我要说话”,他说:“你要说啥?”由于我说话声音微弱,他就蹲在我旁边听,我说:“我想让你跟你的领导反映我这种情况,我是得的乳腺癌,我现在挺疼的,我要回家。”他说:“你把号告诉我吧。”我就给了他家里电话号。我说:“你不相信(我有乳腺癌)我可以给你看。”我就解开衣服给他看了。他看完之后,回头和那帮警察说:“是真的,是真的。”
结果到了晚上九点多钟,来了一个警察,说:把我、吕小薇、吕紫薇、欢欢和姚德义,“他们五个带走,能走的先上车,不能走的拽上车!”然后故意问我:“你是自己起来,还是我们拽你起来?!”我听到这话,自己硬挺着往起站,还没等站稳,两个警察一把拽起我的胳膊就拖走了,当时我乳房疼得几乎窒息,他们把我扔到车中过道上,扑倒在过道上。我疼得坐不到座位上,欢欢和吕紫微把我扶起到座位上。到了五公里拘留所门口,警察又把我拖下车。到了屋里,问完了身高、体重、年龄、得过什么病、多大号鞋,之后让我签字,我告诉拘留所狱警说我有乳腺癌,现在疼得站不起来,我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动了,他们还强行要求我签字。最后欢欢把着我的手签了字。到了被非法关押的屋里,我前胸、后背都疼,不敢平躺、翻身都翻不过去。起不来、躺不下,乳房还出了不少血。
在拘留所,我一再要求看医生,但拘留所拖了我三天也没有医生来看我的病情,还要求让我拿病例。
我乳房痛得哭叫声不断,叫狱警给家里打电话,他们也几番推脱,就这样也不放人。要求见拘留所所长,男狱警总以“所长没来上班呢”为借口搪塞,有一个男狱警吼道:我就是所长!跟我说吧!疼?挺着!(这个男狱警四十多岁,身高不足一米七,肤色黑,方脸)。拘留所的警察看到活生生的乳房溃烂出血的人也不行,非要家属送来(乳腺癌晚期)诊断书才可以。
直到今天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
English Version: http://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14/4/9/9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