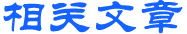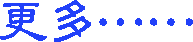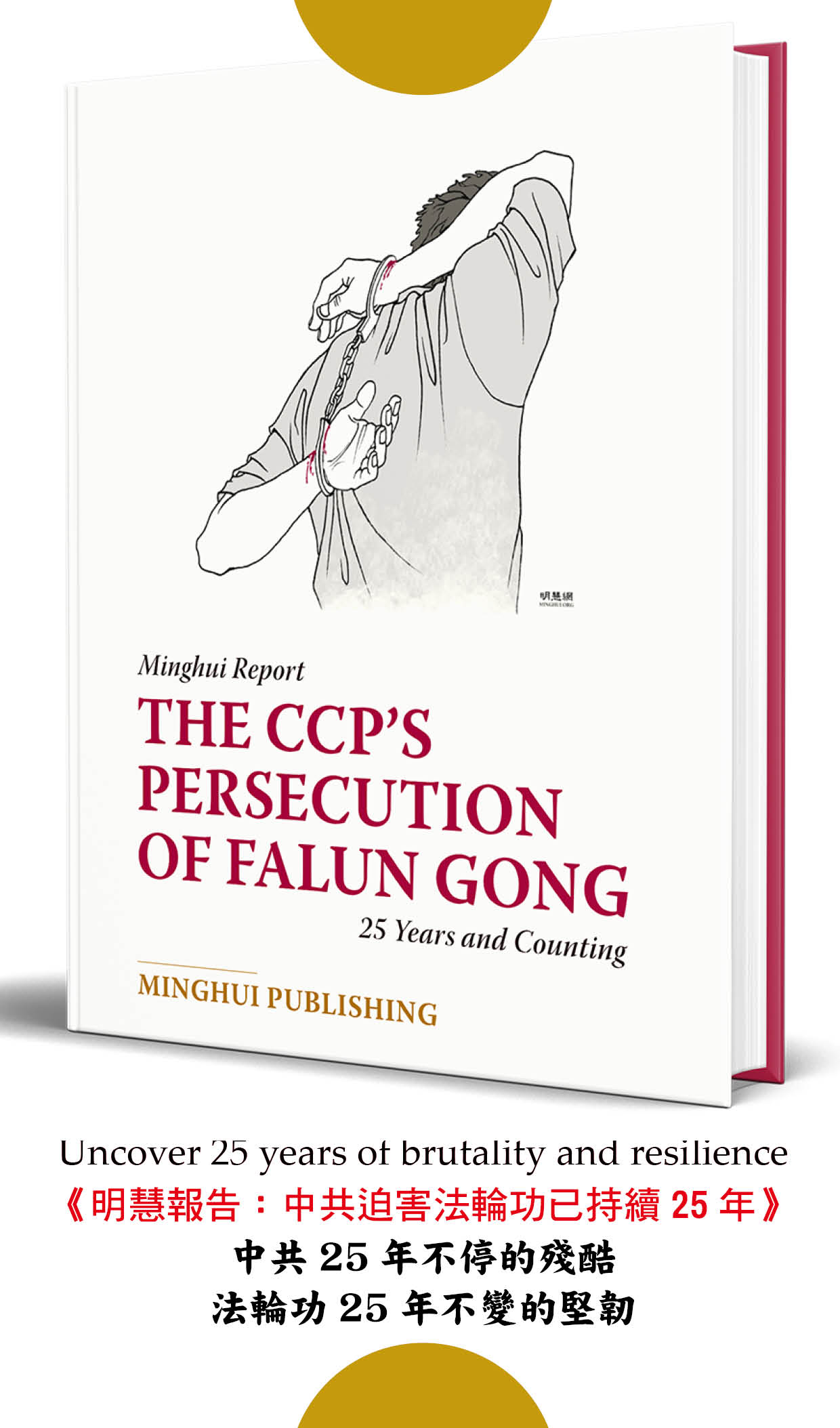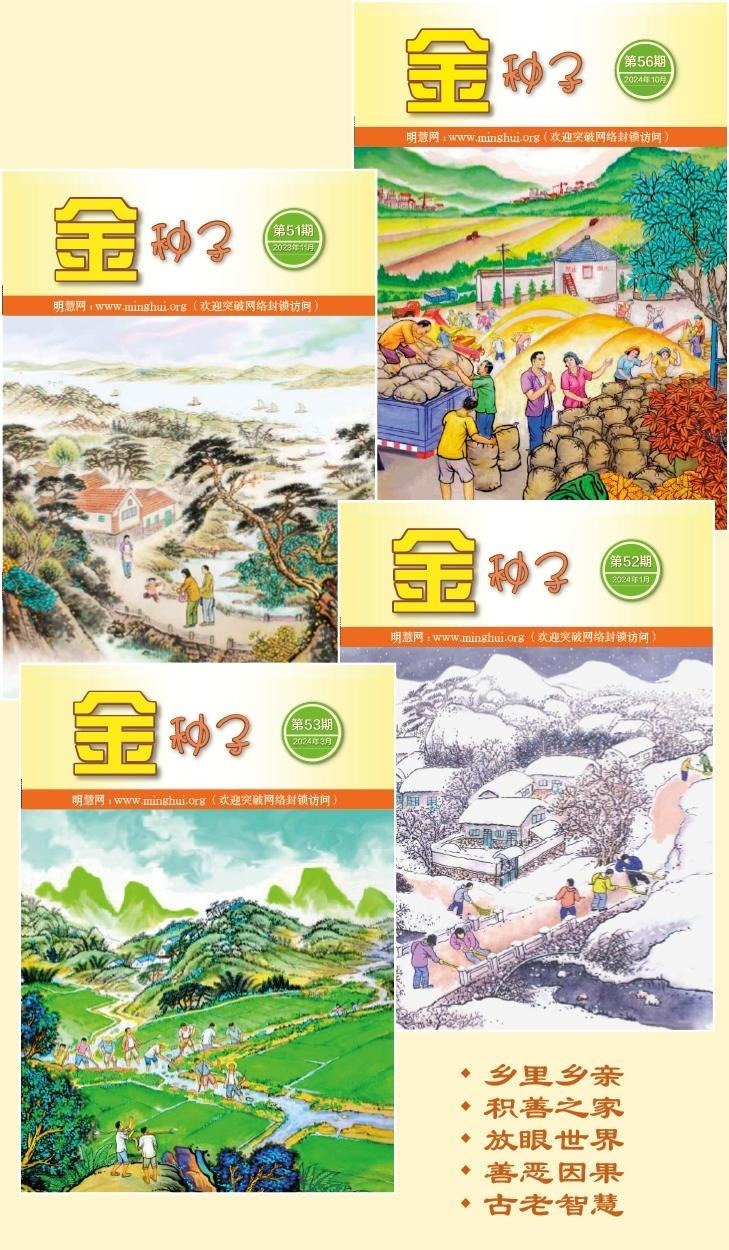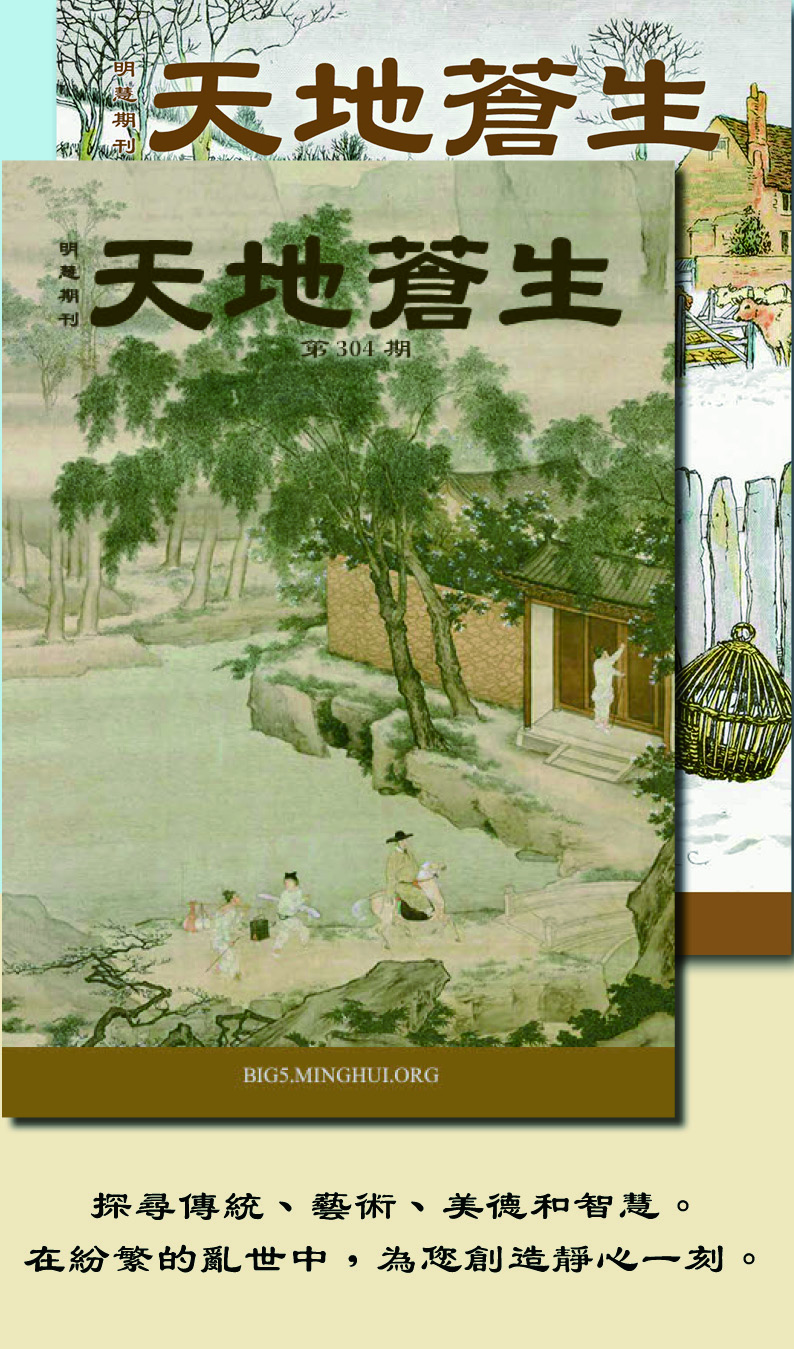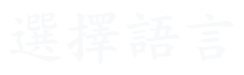狱中见证法轮大法好
回想这段狱中的经历,依然历历在目。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各种怕心、顾虑心等执著心都暴露无遗;修心的过程有剜心透骨的苦和痛,也有被大法熔炼后的幸福与感动,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坚定我对大法的正信。从狱中出来,母亲了解了我的思想后,对来看望我的亲人们这样说:“共产党迫害我儿子有什么用?越迫害他他越坚信。”在狱中我也目睹了中共司法的黑暗和腐败,监狱监管手段的伪善与残暴。不过对这些我并不想多费笔墨,因中共言善行恶的嘴脸早已是世人皆知。现在,我只希望能有一支生花妙笔,尽书我在狱中见证“法轮大法好”的事例。
警察的相机坏了
“六一零”警察把我绑架到看守所时正值下午,那天值班的是个胖警察,他问我:“哪个单位的?”我如实回答了。他有点没好气的对我说:“这么好的单位,学什么法轮功呢?”之后他拿出相机想给我拍照。被抓后一直稀里糊涂的我这时心里忽然涌现了一丝正念,对他说“我不拍”,同时心里想:“让他相机坏,拍不成。”胖警察说:“進了这里由不得你,不拍也得拍。”但当他拿相机强行给我拍照时我见他摆弄了好一会都没拍,只听他嘟囔了一句:“怎么坏了?”他放下相机瞪了我一眼,有点恶声恶气的说:“过那边蹲下!”我没听他的。他瞪着我,语气变的恶狠起来了:“你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不过他见我不配合,最后只是登记一下草草了事,就把我带進了一栋有两扇厚重铁门的地方。
在押犯打我,我不痛
我走过一条黑暗的长长的走廊,两边是曾让我想起来就觉得恐怖的监狱,透过栏栅式的铁门窗,我看到门里的在押犯大多围坐在风场上干活,有的见有人走过也抬眼向我看。我被送進几乎是走廊尽头的某一栋。管栋的警察不在。当身后的铁门“咣当”一声关上时,风场上所有在押犯的目光几乎都集中在我身上。听说是法轮功,一部份人好奇的围了过来,有的可能已听过法轮功真相,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也有人问我:“听说炼法轮功可以成仙,你炼到什么层次了?炼到第九层没有?”——各人问题不同,心态各异,有的觉的好奇,有的因为无聊找话说,而有的却认为我们不正常,希望我语出惊人,找点乐子……。我当时深感共产党造谣宣传对人的毒害。我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暂时放下因身陷囹圄而涌现的各种人心,开始平心静气的讲真相。开始是站着讲,后来有犯人让我坐下来,他们在我面前围坐一圈听我讲……讲的过程中突然有人对我说“栋长让你过去”,我当时还不知所谓的“栋长”其实就是“牢头狱霸”。
栋长正坐在中间监室的屋檐下,块头不小,四、五十岁的样子,头发已经花白。旁边有人让我蹲下说话,我笑笑说:“蹲下说话不礼貌,还是站着说吧。”栋长瞪了我一眼,往门外看了一下,没发脾气,只简单的问了我的一些情况。但下午六点值班警察下班后,五、六个人在风场中间围住我群殴,有的踢,有的踩,我躲开后,他们就追着打。我当时并无怕意,心里默念着发正念口诀,感到全身热气腾腾的,拳脚落在身上竟毫无痛感。晚上收风回监舍我才知和栋长同住一室。监舍很小,象火柴盒,却挤着十七、八个人,里墙的水泥床上睡一排人,床前的地上也睡一排人;屋角是一个没有挡墙的厕所。点名的值班警察刚走,我就被一条肮脏的毛毯盖在头上,随后是一顿拳脚。我没有反抗,照样默念着发正念口诀,照样全身热气腾腾,照样身上毫无痛感。毯子掀开后,所有人都装作若无其事的各做各事,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我也不计较,只若无其事的问栋长:“我睡哪儿?”他安排我睡在下铺(水泥床叫上铺)的厕所旁,每当有人上完厕所用水龙头冲水的时候,四溅的水花几乎都洒在我身上和脸上。那一夜,我反复默念师父的诗句——“身卧牢笼别伤哀 正念正行有法在 静思几多执著事 了却人心恶自败”(《洪吟二》〈别哀〉)。我内心很平静,我感到师父正与我同在,正神正与我同行。
抓住机会讲真相,在押犯认同法轮功
接下来的日子,我需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能否定这场强加给我的迫害?
我以前通过明慧网知道许多大法弟子被抓入狱采用绝食、大声音高喊“法轮大法好”、不服从狱中的任何工作安排等方式進行反迫害。说实话,我当时不大敢这样做,因我怕自己顶不住随之而来的各种魔难。我有各种顾忌和怕心,内心在挣扎。栋长在监舍曾这样警告我:“不准炼法轮功,也不准乱讲话,否则见一次就打一次。”也有人怂恿我:“以前有一个‘法轮功’天天喊‘法轮大法好!’你怎么不喊呢?”还有个从别栋调来的在押犯说:“你们法轮功很神奇的,我们原来那栋有个‘法轮功’绝食了一个多月,一点事没有,管栋警官对我们说谁能让他吃一口饭就免谁的活……。”我很惭愧,我没有这些可敬的大法弟子的勇气,我担心自己做的不好,会落个“东施效颦”的笑柄,给大法抹黑;而且我发现这里的人大多都普遍相信中共的毒害宣传,都用一种有色眼镜看我们,我怕自己把握不好会被他们说成不正常。所以,对栋长安排的活我并没有过多抵制,但也不积极,只是在不紧不慢的做的过程中找机会跟人讲讲真相。但这样做我心是不稳定的,因我拿不准自己这样做对不对,接受干活岂不是承认中共的迫害了吗?
有一次,邻舍的舍长有意来跟我谈法轮功的事,他是因贩毒被抓進来的,他以前也因贩毒坐过牢,而且曾协同恶警看管和迫害过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偏见很大,他说:“你们‘法轮功’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前我坐牢的时候他们都不干活的,也不扫地,都是我们干,可他们却还整天坐谈什么‘真善忍’?你认为这样做对吗?”我说:“一个平白无故的人突然被抓進来坐牢,却只能以拒绝干活作无声而无奈的抗议,你认为这样做过份了吗?他们这样做其实是在反迫害,只是你们不理解而已。”
但经过这次谈话,我越来越感到在这样的环境里讲清真相、澄清误解和偏见才是首要的。我开始定下心来,打算按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主动去接触栋长并跟他聊天,先聊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他的爱情史,然后才慢慢進入讲真相的话题。自以为已经让他对真相有一定了解后,才开始在监舍内公开对其他人讲。而且利用吃早餐前的时间开始炼动功,晚上值班的时间炼静功。栋长都看在眼里,却不再说我。这里要干的活很繁重,大多是针线活和做彩灯,舍里常有人通宵干活,干不完的还被打和虐待。我也常干不完,但栋长却从不这样对我。我知道,世人都有明白的一面,明真相的世人都会同情和敬重法轮功。那位对法轮功有偏见的舍长,常在大家集中在风场上干活的时候来跟我辩论“天安门自焚”、法轮功及共产党好坏的话题,他为了刺激我总是有意维护共产党而挑法轮功的不是,所以有时辩论很激烈,集中在风场上干活的四、五十人大多时候都是在静听,只有我们激烈的辩论在小小的风场上空回荡。我也就利用这种辩论的机会向在场的人讲真相。
随着辩论次数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我明显感到了那位舍长思想的变化和周围环境的变化。那位舍长被判刑接通知要转去劳改栋的当天,他不再与我辩论,而是一直默默的坐在我旁边帮我干活,然后在临出门的时候专门跟我握手道别,并说了一句让我颇感意外的话:“法轮大法好!你改变了我对法轮功的看法,希望以后还能再见面!”原同监舍打我的人(过后我基本知道是哪些人动手的)开始喜欢接近我并和我聊天;有一个还主动要和我合伙吃饭,他怕我记恨,假装问我:“我当时没打过你吧?”我只说“不打不相识”,让他别往心里去。还有一件小事给我印象很深。有个在押犯脾气很坏,谁沾着他,惹着他,他都会还以颜色,或骂或打,有一天早上排队我不小心踩了他的脚,我心想糟了,没想到他猛一扭头听我说了声“对不起”后竟没发火,只平静的回了一句:“没关系!对你们这种人我是很尊敬的!”在这里,他们几乎不叫我的名字,只叫我“法轮功”,我也是第一次以这样的称号公开示人,我一直不敢懈怠,更严格的以“真、善、忍”的标准做人,我怕因自己没按法的要求做会辱没了这个神圣的称号,我知道,我现在的一言一行其实代表的都是法轮功,他们对我的认可,其实就是对法轮功的认同。我以为,对法轮功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一个人的良知。我为世人的良知未泯感到高兴。
同舍犯人学炼法轮功
在看守所被关押的人几乎每天都有人進出,流动性很大。我所面对的讲真相的人也在一拨一拨的换。栋长和舍长几乎都全换了;我和新栋长亦同在一舍。我已记不清自己在这里呆了多少个月,但明显感到形势已是不可同日而言了。同舍的人开始央求我教他们炼法轮功,我也想让他们亲自印证法轮功的神奇,我先跟他们谈了自己炼功的体会,再把炼功可能出现的状态告诉他们:“炼功后一般会出现各种消业状态,比如发冷发热、连拉带吐、头晕肚子痛甚至全身骨头都痛等,这是师父在帮清理身体,都是正常的,一般忍一周或半个月就过去了,然后就可以达到无病状态,一身轻。”同舍十几个人几乎每天都有人跟我学炼法轮功。栋长也带头炼,他很喜欢炼第一套“佛展千手法”,他说炼完后全身舒畅;其他人也都拣自己喜欢的功法炼。有的才炼一两次就出现了消业状态,但他们都是药照吃,功照炼,栋长也这样。有一次警察拿来一瓶药,却倒不出药,药粒沾在瓶里面了。警察走后我对他们说:“吃这种过期的药有啥用?吃了不一定好,不吃还可能好。”
有一个因讨薪械斗伤人一审被判无期的农民工,跟我炼静功后也出现了较严重的消业状态,发冷发热,头晕咳嗽,痰里还带着血丝,半夜常捂着肚子拍醒我,问:“肚子痛得要命怎么办?”我跟他说:“这种状态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你若觉得自己熬不住你就去吃药,但你若觉得自己行也没关系的,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心里不能想你的病,只当是过关好了。”但没想到他好象铁了心,一粒药也不吃,照样常跟我炼静功。大概过了一个多星期吧,他终于熬过了清理身体的痛苦阶段,后来他身上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就是他每天身上都有不同的穴位在跳动,他说很舒服。有一次他坐在我对面干活,突然指着自己的大腿说:“你看,这个穴位又跳了!”我瞥了一眼,果然看到穴位处的衣服在动,但我只是淡淡的说了句:“这种现象很正常的。”
其实我们共炼法轮功的场面没持续多少天,因某天晚上大家在床上围坐一圈炼静功的时候,被值班警察通过录像镜头发现制止了。第二天我被管栋警察叫去谈话,让我保证以后不再炼功。我没答应,只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不会让你为难的。”他没处罚我,我知道他心里其实很同情和尊敬法轮功,他曾偷偷对我说:“共产党坏谁都知道,但心里知道就行了,不要说出来。”栋长也被叫去谈话,并让他监管我不让我再炼功;后来栋长告诉我他是这样回答警察的:“共产党都管不了他,我哪里能管住他?”那个常跟我炼静功的农民工也被警察叫去训了一通,说在录像里看到他跟我炼的最多。农民工吓的不敢再炼了,但他说以后下劳改场再炼,而且这辈子他炼法轮功炼定了。我为不把事闹大,也改到风场上炼功了;晚上回监舍也不再明目张胆的炼,但舍里的人常围坐一圈玩牌有意挡住镜头让我炼。
法轮功是个神奇的功法,但若只是“人云亦云”,所感知的自然是盲目和浅薄的,只有亲身实践,才会有深刻的体验。同舍的人跟我学炼法轮功虽时间极短,只是浅尝辄止,但却足以改变人心。较明显的变化是,舍里原先常虐打犯人的现象几乎没有了;有的问我出去后怎样才能找到法轮功,他们说也想学法轮功做个好人;有的一有空就来央求我讲法轮功的事,我在风场上炼功他们也主动为我放风。总之,他们对法轮功了解得越多,就越尊敬法轮功,许多人的确也因此有了弃恶从善的一念。有一个曾跟我呆过一段时间的抢夺犯被判刑后转到了劳改栋,他被释放经过我所在的关押栋铁门时,竟不理会身后还跟着警察,跳起来往门内望了一眼喊道:“‘法轮功’还在吗?”
念大法好,老谢的糖尿病好了
老谢(化名)是半夜被送進我所在的监舍的,第一次见到他,我对他的印象很不好。他大概五十多岁,有点肥胖,眼小脸大,一头蓬发。他对人爱理不理的,只跟人说本地话,不说普通话。栋长开始用普通话问他话,他大多不理不睬,栋长以为他听不懂,问他:“会说普通话吗?”他却用普通话回答:“不会。”后来因这事我们都称他“老顽童”。他進监舍的当晚,从四点开始就一直咳嗽到天亮,一舍人都睡不好。此后几乎一直如此。而他每天照抽三、四包烟,连在水龙头下冲澡嘴里还叼一根烟。
就是这样的人,每天开饭却喜欢蹲在我旁边吃。他也知道我有点嫌他,每次他加菜都是往自己碗里倒一半后就把加菜的盆放到我面前让我吃,我一推托,他就闪开了。这样一来我反而不好意思了,几次下来我只好邀他和我合伙吃,但前提是大家轮流加菜。本来自我被抓后家里经济很困难,新婚不久的妻子怕我受苦却总省点钱寄给我;我常深感对不起家人,而我在这里所能做的就只有少花家里的钱。所以我一向不大喜欢和人合伙,尤其是和老谢这样的人,因我知道他一進来就带有几千块钱放在帐上。果然,每次轮到他加,他都是加那些很贵的肉菜,加最多的是烧鸭,半只二十五元;而我大多只能加一些素菜。我很不安,想跟他分开吃了。他却很坦诚的告诉我,他从小就在社会上混,阅人无数,一见我就知我是个很善良很值得信赖的人,如果我跟他分开吃就是看不起他。我不好再说什么了,心想,他大概是跟我有缘吧。他不大识字,人也有点懵懵懂懂。我跟他讲法轮功真相,他说他在外面看过自焚真相光盘了,他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很好。有一次舍里的人在看共产党的宣传晚会,我问他爱看这种晚会吗?他却说:“我宁看黄色录像也不看这种东西的,看太多这种虚假的宣传会害死人的!”然后他结合他的亲身经历跟我谈对共产党的看法。我听后很惊异像他这样的人竟会对中共的邪恶本性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我对他说:“可惜你没看过《九评共产党》,否则你一定会发现你的一些观点书中都提到了。”
我知道老谢身体不好,但一直没问他有什么病。有一次见他脸色发青在风场上晕倒才知他有高血脂和很严重的糖尿病。他说他在外面每天都要吃药的,现在没药吃才这样。他让我帮他向管栋警察写一份住院治疗的申请书,并帮他写信回家要药要钱。但住院申请写好后,舍里的人却都劝他不要去住院,说上次有个人才去医院住了几天就花了五、六千块钱,病也没见治好,比抢钱还厉害。老谢听从了众人的劝告,只等家里寄的药。几天后他家就寄来了治糖尿病的药和验尿的检测纸。我问老谢怎么会得糖尿病呢?他说他也不知道,只是有一次在地上撒尿见有蚂蚁爬才去医院检查发现的。他说他一停吃药头就晕,吃糖也晕。我说烧鸭也放有蜜糖让他以后不加这菜了,他却说:“進这种地方也不知什么时候死,还是趁活着的时候多吃点好吃的,死也值得。”
老谢也许是听我常跟人讲真相时多次提到炼法轮功可祛病健身不用吃药的话了吧,有一次傍晚放风散步的时候他竟颇认真的来央求我教他炼法轮功。我没有教他炼功,却教他另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诚念“法轮大法好”。说实话,我还从未让人试过这种方法。我坦白的对老谢说:“我以前也只是从明慧网上看到过念‘法轮大法好’也能消灾祛病的事例,我还没试用过,不知你信不信,你可以试一下,看行不行?”没想到老谢却很认真的对我说:“我很信的。怎么念?你把这句话写在纸上给我。”晚上回监舍后我用信纸写了“法轮大法好”,并用普通话教他念,他却问我:“用本地话念行不行?”我想了想,说:“应该行。大法只看人心。”
此后几天我注意到老谢早早就起来坐在床上默念“法轮大法好”了。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竟完全忘了这事了,每天照样象往常一样消磨时日。这里有两句话最流行,一句是“起得比鸡早,干得比牛多,吃得比猪差”,一句是“日子难过天天过”。这样的日子也不知过了多久,一天,老谢忽然来对我说:“我好象已经很久没吃药了,刚才小便我用检测纸验尿,显示的竟是正常,我是不是好了?”我这才开始注意老谢的变化,我发现他比以前更精神了,吃东西也不再忌口,除了吃烧鸭,他也常买香蕉和苹果吃,而且不再吃药了;烟他照样天天抽,但晚上已不见他咳嗽了。舍里的人也逐渐发现了老谢的这种变化,都说“老谢進来坐牢竟把病坐好了,变得越来越健康了。”我没有跟其他人说老谢是念“法轮大法好”好的,但老谢心里知道。他让我出去后一定去找他,他要好好谢我呢。
再次见证“法轮大法好”
我第二次见证诚念“法轮大法好”即消业祛病的事例是被判刑调到劳改栋之后。
進劳改栋的当晚我就在舍里讲真相。第二天同舍一个吸毒的犯人走过我身边时迟疑了一下,停下来问我:“昨晚睡觉我试着念一会儿‘法轮大法好’,感到被窝里热烘烘的,今天我起来的时候发现脚后跟长的那个毒疮好象小了点,而且可以脚跟着地了,原来我吃了很多药都没什么效果,这是不是因念了‘法轮大法好’的原因呢?”我只笑笑说:“也许吧。是真是假,你可以再试试看。”大概又过了两天,他有点兴奋的来找我:“我一直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第二天我脚跟的毒疮竟流血流脓,第三天竟变得越来越小,现在几乎全好了!你看!”他伸脚想脱鞋给我看,我用手制止他说:“不用了。我知道是真的。”他问我法轮功怎么炼?能不能教他?他说过几天他就要被释放了。我说:“一切随缘吧。以后出去你能时时诚念‘法轮大法好’,也是一样的。”
中共有意迫害文化层次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大法弟子
入监后,我被送到一个监狱集训一个月。
入监前,来检查行李的维纪(帮警察协管的犯人)听说我是法轮功,竟有点好奇的马上问我:“是什么文凭?”我说是“大学本科”,他们好象颇惊讶的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使我想起了第一次开庭后一位年轻的法警让我签字时偷偷问我的话:“奇怪?你们炼法轮功的怎么都是一些文凭很高的人呢?”我记的在看守所“六一零”恶警来提审我时曾假装关心的问我:“你平时是不是精神很空虚,要不怎么会炼法轮功呢?现在炼法轮功的都是市场上那些不识字的卖菜的阿婆之类的人。”但在看守所,我在门口曾听到管栋警察与另一个警察聊天时说:“刚才又進来一个法轮功,是个研究生,而且是××局的,奇怪?现在炼法轮功的人怎么都是那些单位又好、文凭又高的人呢?”现在从维纪的神色,我基本可以确定:有许多这样的大法弟子也被抓進这里迫害了。后来的事实的确印证了我的判断。在我见到的、听说的在这里被迫害的大法弟子里,几乎全是文化层次较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律师,有的是法官,有一个竟然是某市原“六一零”办公室主任。在我将出狱前,某狱警向我透露了一个信息:现在的法轮功学员有知识有文化,影响力太大,被定为高危份子,都是监狱严管的对象。我当时心想:“炼大法的人其实遍布社会各阶层,什么样的人都有,也很多,而近期被抓的均是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看来绝非巧合?”我猜想,共产党是有组织、有预谋、有目地的针对这群大法弟子進行迫害。
管教谈话走过场,犯人敬重法轮功
在监狱,管教好象都有任务要定期和法轮功学员谈话并做记录,所以我常要面对的就是与警察的谈话。但我发现许多警察都是应付了事,有的一开口就对我说:“你什么都不用说,你想说的我都知道,也都明白,如果是在外面,我们可以象朋友一样畅所欲言,但在这里我只能说我该说的话。”有的管教干脆连谈都不谈,只做假记录交差。但有一次与一位监狱领导的谈话颇让我意外,他问我:“我好象都没迫害过法轮功啊?听说我也上了你们的‘国际追查黑名单’?怎么会这样呢?”他语气显得有点委屈的样子。我说可能是在你管辖范围内发生过迫害法轮功的事吧,你作为领导当然是脱不了干系的。他又问我:“《九评》讲的是什么内容?如何才能看到?”我说共产党现在网络封锁很严,要有一个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才行。他又问我如何才能得到软件?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如果你还有缘的话,你会得到的。
与警察的交谈,使我明显感到了形势的变化:迫害是越来越见不得光,越来越不得人心了。在与犯人的相处中,我所看到的法轮功的形势与我在外面所感知的也是天壤之别。有的犯人竟能背诵师父的诗句;有的一见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有的找我想学法轮功。有个有文化的经济犯,他很尊敬法轮功,他让我们平时讲真相一定要注意安全,他说他知道中国现在的许多形势都是法轮功讲真相推动的,法轮功既是在反迫害,其实也是在为大多数中国人谋求合理合法的生存环境。我说:“可惜有你这种见识的中国人太少了。”
诚念大法好,老贾病业消,炼功做好人
睡在我下铺的老贾(化名)是个病号,他因诈骗已多次坐过牢。他诚念“法轮大法好”也出现了消业祛病的状态,有时半夜都见他难受得在床上呻吟,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说他身上的病好象都翻出来了,连以前被警察打伤过的地方现在都痛;有一次他把衣服掀开让我看他的肚子,连肚子都鼓了起来,他说他以前肚子有病。他还有严重的高血压,有一晚竟晕倒了,惊动了监狱的领导,第二天安排他去医院检查,他问我怎么办?我说让你去你就去吧。他检查回来后,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真是怪事!我去医院的途中还很难受,一進医院却又感觉好了,一检查,啥事也没有!但一出医院,回来又难受了!”他大概难受了半个月,身上所有的病症突然消失了,他从此精神起来,不但走路生风,也开始起来晨跑了。有一次他提着两个水壶,学着以前轻手轻脚走路的样,对我说:“你看,以前我是这么走。”然后他拿起两只装了半桶水的塑料桶学着少林寺和尚炼功提水的样,并有点夸张的高踢起一条腿说:“现在是这样走!”
此后他常央求我跟他讲法轮功的事。他对法轮功越了解,就越敬重法轮功,他常这样感慨:“没想到法轮功这么伟大!”以后他一见人议论法轮功就会用手指着对方的鼻子说:“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法轮功!”一天他很认真的跟我说:“我想全心投入你们法轮功,你们叫我去做什么我都会去做!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我都干!”我苦笑了一下,说:“看来你也信了共产党造的谣,以为我们是什么政治组织吧,其实我自己都是看书自学的,几乎不认识其他人,而且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自觉自愿的,没人叫我怎么做。如果你想学法轮功我可以教你,但以后你要做一个好人,不能做坏事了。”老贾很诚恳的对我说:“我行骗多年,一辈子胡说八道,以后我要洗心革面,学法轮功做个好人!”
我于是用了几乎两个星期的时间,教老贾学会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老贾一炼起来就说感觉非常好,一有空就想炼,有几次我见他在公开场合竟也旁若无人的比划着炼功动作;在十几个人住的集体宿舍,半夜他竟也爬起来坐在床上炼静功或躲到冲凉房炼动功。一天早上他告诉我他昨晚在床上炼静功被值班维纪发现了,我问是谁,他说了一个名字,我听后说:“没事,他不会告发的。”其实那维纪常听我讲真相,而且已经打电话回家让当警察的父母都退党了。那天他打完电话后就来对我说:“我打电话回家想叫我爸妈退党,开始我以为肯定很难说的,因为他们都是警察,谁知我刚跟我妈一提这事,她竟有点迫不及待的问我怎么退?她说最近看到中国异常天象不断早感觉不对头了。我把你告诉我的退党方法告诉她了。我妈让我找机会也跟你学法轮功,回去后教她炼。”
老贾炼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他竟对我说:“我想出去公开炼功。”我当时还有怕心,对他说:“这样的话可能我就被关禁闭了。而且还会被严管,讲真相就更难了。”他听从了我的劝告,说出狱后再到公园公开炼功。
法轮功正在创造神话
在狱中,说到“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听的人基本能接受,因这已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一说起“天灭中共,退党保命”的真相,大多人却认为不可能。我也知道,要让人相信一件未来将发生的事,是不容易的。有时说不通我就这样讲:“其实对法轮功所讲的,你可以这样来判断:要么真,要么假,假的,就是在搞一个天大的笑话;真的,就是在创造一个神话。但你可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那么多电视、那么多报纸、那么多网络、那么多大法弟子都在全力讲这个真相,而且许多大法弟子为讲这个真相被迫害入狱,甚至失去生命,你认为有可能是在开玩笑吗?如果最终证明是真的,不信的人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后果太严重了!”
其实发生在大法弟子身上的奇事、奇迹是难以尽书的,而每个大法弟子修炼中身心净化和升华的奇妙体验更是难以言传。在个人修炼中,我对大法的神奇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验,有时在狱中炼功,在身心不断升华的震撼中,我会莫名的被感动而泪流满面。我知道,对我们这种修炼状态,不修炼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理解,但我内心清楚,自己的信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修炼中一步一步连滚带爬的修出来的,其间的心情难以言喻。
真的,如果我能够,我愿用我的生命见证:法轮功正在创造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