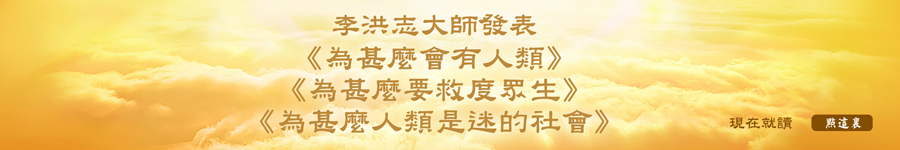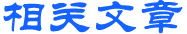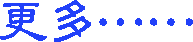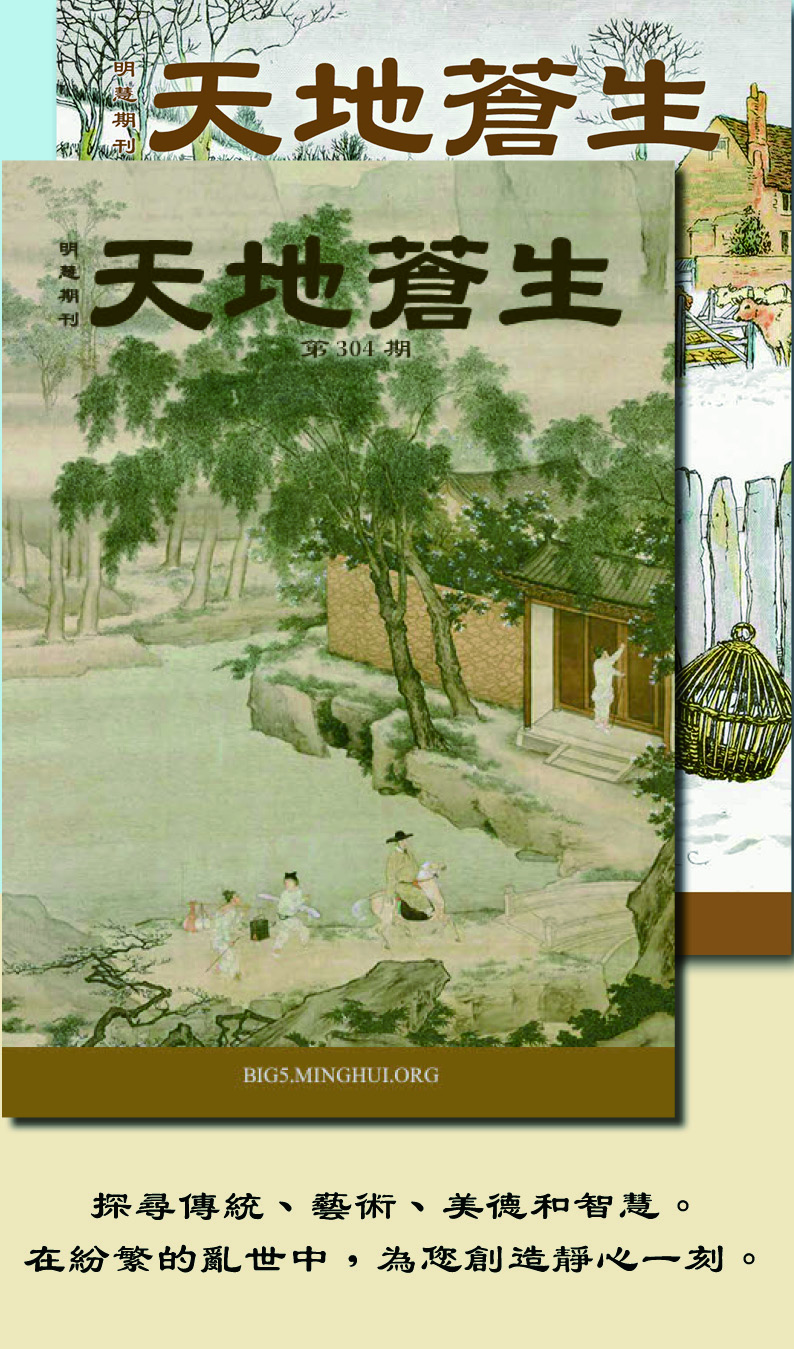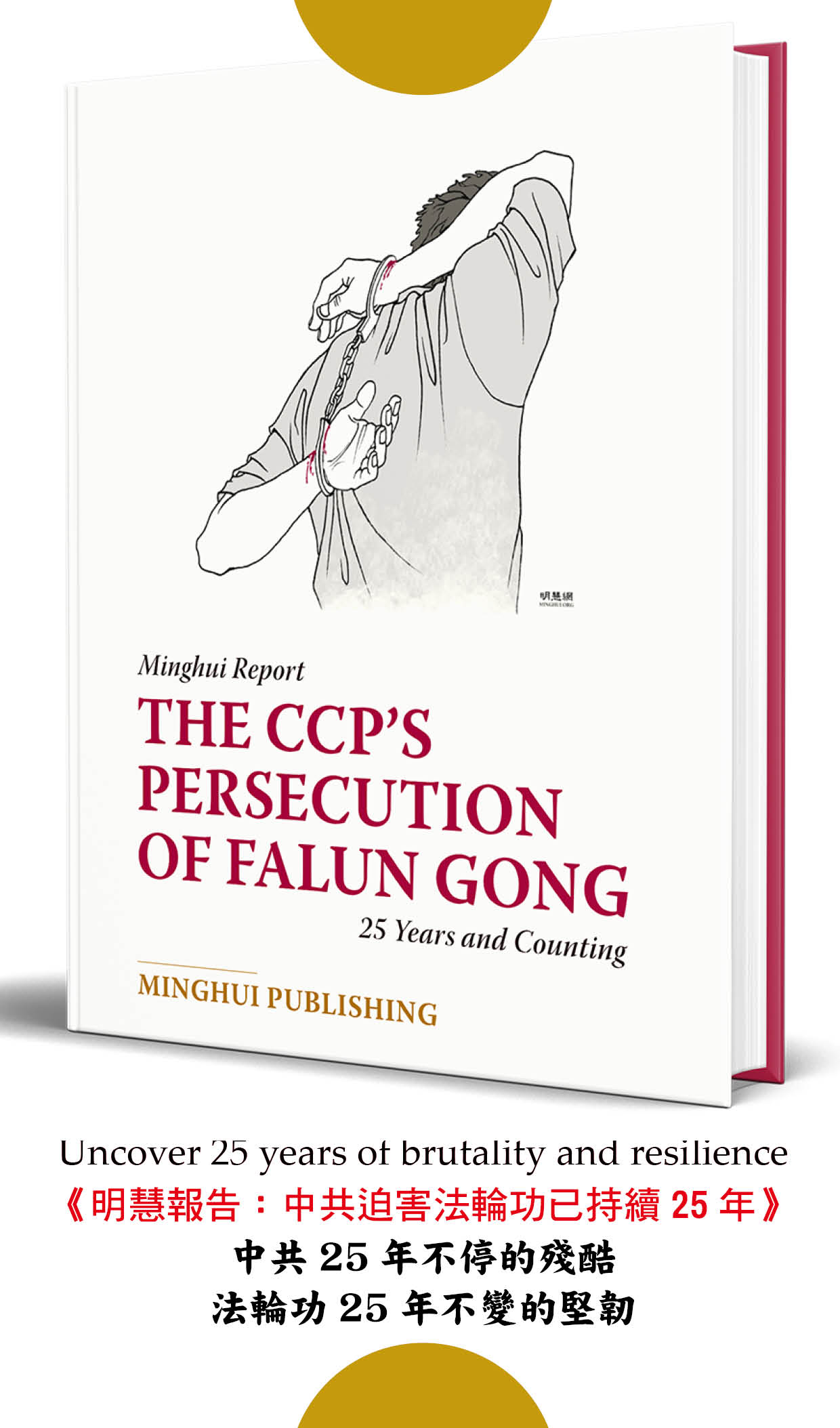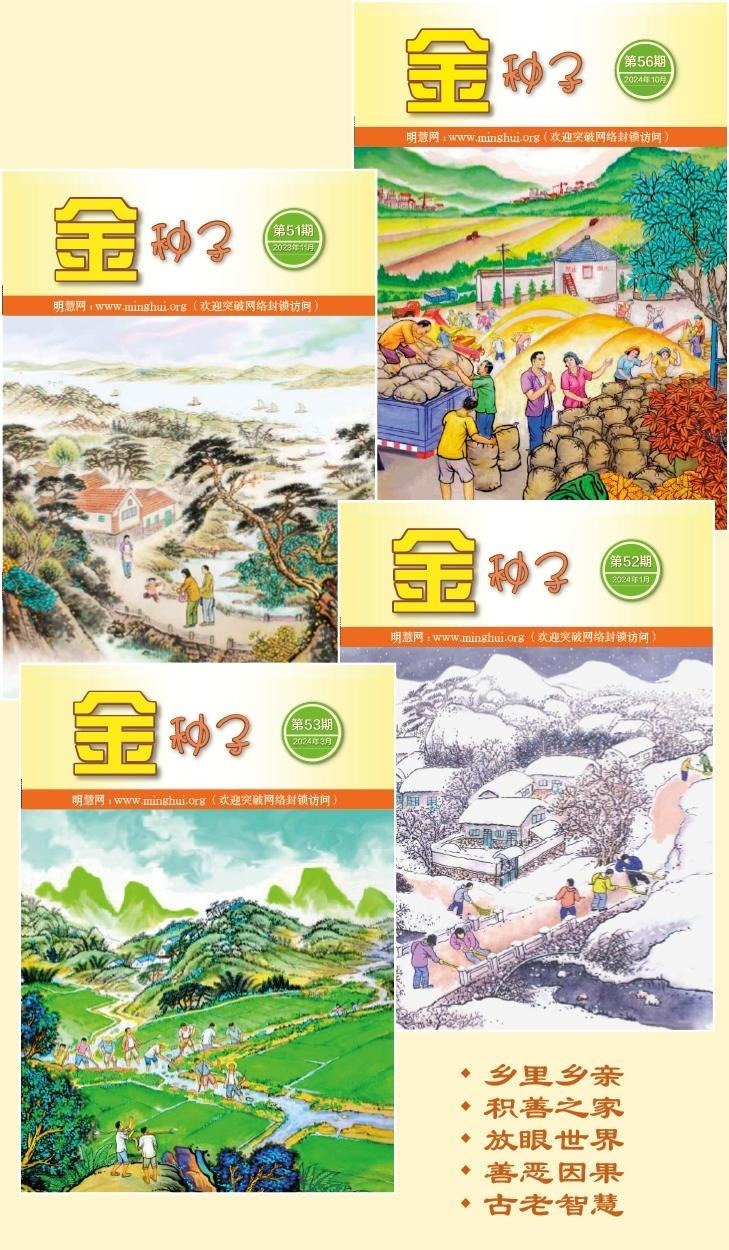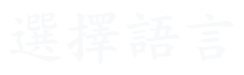破晓(二)
希望能唤醒他们的良知
功友趁接见送东西之机智慧的为我们送進了一本《转法轮》,我们互相传看。这天晚上三楼一室的朱丽正在学法,被中队干事带上民管会的人来抢走了大法书,它们还把朱丽用绳子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得知这一消息,我们都没有去集合场炼功,趁吸毒人员洗漱之机,去陈祥芝寝室,大家的心是那样的痛,没有了大法书,怎么学法,我们集体签名写信要求詹队长还给我们大法书,又推荐陈祥芝作为代表找詹队长讲真象要求还书。结果仍然要不回我们的大法书。
痛苦之余,我们十四个大法弟子决定集体绝食。由于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绝食,没有想到绝食是那样的痛苦,前三天我只感到一阵阵的饥饿、难受,第四天我已严重脱水变形,眼皮发皱,眼窝深陷,脸、手都是皮包骨头,皱巴巴的,两鬓的头发开始发白,而且我胃里翻出来的脏东西恶臭难闻,让人一直恶心呕吐,连唾液都无法往下咽,我静静的躺着背法,难受的症状缓解一点,就急忙下床炼功。
到了第七天我所有的欲望和身体难受的症状全消失了,又能静静的躺着背法了,我每天早晨照样去陈祥芝寝室,鼓励大家坚持绝食。第九天,民管会通知我们中队警察表示不再收缴我们的大法书,我们可以在寝室里自由的看书学法,而且我们可以在走廊上集体炼功,它们也不管了,于是我们结束了九天的绝食。
但是为了获得不被长期锁在寝室里;为了争取能走出中队铁门到操场上集体打坐炼功,我们仍然不吃从窗户缝里递進来的饭。因为每个中队去吃饭都要经过操场,我们要带动全所的大法弟子都出来堂堂正正的集体炼功。朱丽和陈祥芝把功友来接见我们时送進来的花生米分给大家,一人一点花生米。我不知道这段日子会坚持多长,于是我每餐只吃七粒花生米,喝一大瓶凉水,每当吸毒人员去吃饭了,我也将花生米拿出来数。有时候抓在手里的花生米是九粒,我便自动的退两粒放回去,其实我心里多想吃上一把花生米啊。但是花生米只有那么一点点,这是维持我生命,能有充足的精力,维护大法用的,不能多吃,我严格要求自己,吃一粒花生米喝几口水来填饱肚子,我心里跟师父说:“师父,弟子好想吃顿饱饭啊。”在这样邪恶的环境里,弟子们为了维护大法,争取自由,虽然忍受着难熬的饥饿,但是心里始终充满着幸福和快乐。因为我心中装着的是“真、善、忍”宇宙大法。虽然人瘦得皮包骨头,但是精神特别好,每天学法、炼功状态都非常好。而且脸色特别红润,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加持。这样又坚持了二十七天,詹队长叫民管会打开了我们长期关闭的寝室门,要我们同吸毒人员一起去劳教食堂吃饭。
从此我们全中队楼上楼下的所有大法弟子可以自由的集体学法交流了,连吸毒人员和杂案都无比高兴,她们也可以自由的去串寝室了。
我们终于有机会走出三中队的大门,去操场炼功了,这是我们三中队全体大法弟子的心愿。每次吃完饭返回中队时,我们就在操场上打坐。我看见前面的杨启慧、潘广平、朱丽等都分别被拖回中队。杨启慧,她人又瘦又小,在被拖回中队的途中,她的腿仍然双盘得好好的。我跟同寝室里的吸毒人员和杂案们讲真象,她们都明白我们去操场打坐,是为了证实大法。虽然詹队长叫她们每次由两人左右臂包夹我,但我每次都能挣脱她们就地盘腿,她们还保护我不让其它寝室的吸毒人员来打我。这天中午去吃饭时我就想,我回来就去蓝圈前面的大圆圈里去打坐,刚走進操场,我以最快的速度挣脱她们進入圆圈里盘腿,虽然当时我穿的旅游鞋都未脱,还是那样轻轻的就盘上了腿,我感觉当时腿特别的轻,特别的软,双手结上印时,我感到是那样的祥和、美好和殊胜。我静静的坐着。这时我听见了小蒋和阳阳在小声的叫我:“周姐,该‘合十’了,你们功友都被拖起来了,就剩你了。”我双手“合十”睁开眼睛,阳阳帮我扳下了双腿,陈洪容她们把我扶了起来,我们全寝室的人将我团团围住,因为怕民管会和其它寝室里的吸毒人员来打我,我真为她们能明白真象善待大法弟子而高兴。她们还告诉我,刚才一中队的法轮功看见我们打坐,她们中有一个也在打坐了。
四月初八是我们师父的生日,我们写书面请求要求召开一次心得交流会。队长詹丽不同意,于是我们所有的大法弟子又集体绝食三天,要求还给我们信仰自由,无罪释放我们。
不交书遭酷刑
六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室长陈洪容告诉我:说劳教所又购進许多手铐、电棍,在每个中队挑选最狠的吸毒人员去当“民管会”来整法轮功学员,全所最恶的警察张小芳去当队长。每天他们收工回来都为此事议论纷纷,听说在医院方向专门准备了旧房子,用于关押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要关在小间里。六月十九日我们得到可靠消息,恶警对全所的法轮功学员進行封闭式管理。于是我们中队的十九名大法弟子,把功友带進劳教所平时学的《转法轮》和师父的《新加坡讲法》,想办法带走。功友蒲有翠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她把自己的被面缝成小书包,每个大法弟子将小书包贴身挂着。
当时分给我的是《新加坡讲法》,我心里想一定要保护好这本大法书。六月二十日早晨五点多钟,我就起来收拾东西,把书包挂在脖子上再拴在腰上。早晨刚起床,民管会就通知我们全体法轮功人员带上东西到中队集合场集合。刚下楼就看见护卫队的男警察站了一排,胳膊戴着红袖套,腰间挂着手铐、电棍、狼牙棒等刑具,还有一排所里的干部站在那里,我们的东西全部被放在集合场下面的沼气池旁边,刚放下,警察就开始拆我们包好的被子,搜我们的经文等东西。
我们十九个大法弟子站成两列分别被叫去一个一个的搜身,轮到我了,把我叫到底楼的洗澡间,所里女干部警察叫我脱掉衣服搜身,我告诉它说:“我身上有经文,不脱衣服。”这位警察叫我把经文交出来,我说:“我不会拿给你。”心想:哪怕是失去生命我也要保护好大法书,绝不能把大法书交出去。于是我们僵持了一阵,没想到它大吼一声:“护卫队,这里有一个顽固的,不交书。”很快护卫队的几个警察就冲到门口来了,它们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我,突然冲進来,把我踢翻在地,然后,把我双手反铐着,并拉着手铐把我从洗澡间一直拖到集合场下面的沼气池坝子里,拖了足足几十米远,因为走廊的地面都是凹凸不平,我的裤子被拖掉了,臀部的肉皮被拖掉了大片。大法弟子杨启辉哭着跑来帮我把裤子拉上来。它们把其余的大法弟子转移走了,等其他大法弟子一出中队大门,两个警察又把我拖上集合场,把我的双手反抱着大树铐起来。所里的警察毛伟就用电警棍电我的胳膊。那天吸毒人员全部没有上工被锁在寝室里,他们听到电警棍电我的声音,都扒在窗户上大吼:“周姐,它们要电死你的。”我抬头看见我寝室的陈洪容她们都在吼,阳阳也边哭边吼,我微微的向她们摆了摆头,示意她们别怕。毛伟的电棍电流开到了极限,也未能掩盖住她们的哭喊声。我被电完了左臂,又电右臂和双手,就这样足足电了我几十分钟,我强忍着剧痛一遍一遍的背着师父的经文《无存》:“生无所求 死不惜留 荡尽妄念 佛不难修”最后毛伟电累了,说:“你别坚强,我等一会儿再来收拾你。”他就坐在我旁边的大树下去喝水,我仍默默的背着经文《洪吟》。毛伟又叫一个民管会吸毒人员邓丽拿脏毛巾来塞我的嘴。
七中队开始对大法弟子進行血腥镇压
警察和民管会的人员卡着我的脖子反扭着我的手臂把我转移到新成立的七中队。刚進七中队大门,干事李军就过来狠狠的打了我几耳光,然后叫三个民管会把我拉去吊起。于是民管会跑过来几个人把我吊铐在中队底楼一间屋子的铁窗上,整个下午我听见隔壁屋子里都在用警棍电人,电了一会又问:“报不报数。”没有人回答。后来才知道是电大法弟子——攀枝花的教师温跃超。吃晚饭的时候,我听集合场队长李坤容在骂人,功友在抗议:要求见到我,她们就吃饭。我要求上厕所,它们仍然把我的双手铐着,由两个吸毒人员和一个警察把我押去上厕所,吸毒人员给我脱裤子,我臀部被拖烂的肉和裤子粘在一起都干了,它们使劲拉裤子,受伤部位钻心的疼痛,一片血肉模糊,她们看我伤得很重,才去报告教育科李志强,晚上把我放了。就这样折磨了我一整天,滴水未進。
六月二十一日早晨六点多钟听见楼下队长李坤容在骂人,我和宜宾大法弟子杨旭到窗前一看,有的功友被吊在水泥桩上,有的在挨打,由于我们的寝室门被锁着,我和杨旭便拍玻璃窗,叫它们不准打大法弟子,没想到把玻璃窗户拍碎了。李坤容气势汹汹的叫民管会把我们全室的七个人叫下去,站成一排,诬陷我们想翻窗造反,叫吸毒人员打我们。李晓林是同性恋吸毒人员,它脱下它穿的男人的皮鞋挨着一个一个的用皮鞋抽打我们的脸,我们的脸被打得通红。
整个上午,底楼的几间小屋和集合场到处都在毒打昨晚在寝室炼功的大法弟子,电警棍发出的啪啪声到处都是。我的心里难受极了,心想:我们不应受这样的迫害,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炼功,修炼真、善、忍是没有错的。于是利用大家集合完回寝室的时间,我向同修谈了我的想法,大家都觉得应该在集合场集体炼功,因为集体炼功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警察叫我们蹲下报数,我们就盘腿打坐。接着大部份大法弟子都在盘腿打坐。这时几个护卫队的男警察加上十七个民管会的人以及中队的七个警察全部都来打我们,七、八十个大法弟子被他们乱打乱踢,被警棍电,狼牙棒抽打,但是我们仍然坚持炼功。当时我被拖烂的臀部肉已腐烂,功友邢兵拿出了卫生巾,温跃超替我贴在受伤部位。我们被警察踢翻了又慢慢爬起来再盘上腿,这样反复被打了几十分钟。中午吃饭又叫蹲下报数,于是我们又开始盘腿打坐,它们全部又来打我们。我受伤的臀部被踢得疼痛无比;大法弟子毛均华被电晕了过去,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前排的大法弟子张玉春、白合林被打得脸都变形了,嘴歪在一边,眼睛都无法睁开。我们就这样一天三次报数,三次炼功,三次挨打,每次都是几十分钟,很多大法弟子为此被打得遍体鳞伤。
队长李坤容又开始变着花招迫害我们,叫我们站军姿、走正步、跑步。六月底天很热,从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二点长时间的折磨我们,挨打挨罚。它们还在每个寝室挑选几个功友弄去单独用竹块打,我寝室里安岳進修校的英语教师王红霞和攀枝花的教师温跃超被打得整个臀部全部都成紫黑色,乐山的李凤其是被脱掉了裤子打的,用一把一把的竹块打,她的臀部整个都是血肉模糊,多处都是小指深的伤痕,肌肉都被全部拉掉了,只能爬在床上由功友用一条裤子给她盖住。看到李凤其被打成这样,我的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并急速到二楼的其它几间寝室叫功友去看李凤其被迫害的惨状。三楼的老功友刘国平正在洗澡间洗衣服,我告诉她李凤其被打成什么样了,刘国平听后流泪了,她很快回到三楼告诉了功友,当时我只希望功友们看到李凤其被打的惨状,更能坚定我们继续开创炼功环境的信心。功友们都陆陆续续来看李凤其,中队警察就叫民管会把李凤其弄走了,后来才知道被关在了底楼的屋子里。
坐 军 姿
我们全体大法弟子又被罚“坐军姿”,被强迫听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的录音。我们被强迫坐在二十公分高的小塑料凳上,小腿和大腿成90度,大腿和腰成90度,两手平放在大腿上,两眼平视前方,腰直颈正,不准晃动,不准闭眼,嘴闭上,从早上六点过坐到晚上十一点不准喝水,就这样坐在集合场上晒太阳。每天坐不到半小时,臀部象针扎一样的剧痛,却不敢动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走廊上有一排护卫队,腰间挂着狼牙棒、电警棍、手铐等,虎视眈眈的盯着我们,还有十几个民管会和中队干警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谁一晃动,或腰稍微不直,它们立即就是一脚踢过来。罗治玉、杨旭等功友几次被踢翻在地,我前面有些年岁大和身体胖的功友不时的被踢翻在地,罗治玉功友已经50多岁了,晚上她实在受不了,便动了一下,民管会的人便将半瓶冰冻的矿泉水连瓶带水向她砸去,顿时罗治玉的额头鲜血直流,它们便把罗至玉拖出去,叫朱锐给她包扎好,又把罗治玉被血染红的白衣服脱下来丢了。
我不断的听见功友被踢被打的声音,虽然我的臀部疼得象针刺一样,也不敢动一下。七月份,天实在太热,早晨未坐到半小时汗水就开始从头发尖上往下滴,滴到手背上、裤子上,中午眼前热浪翻滚,汗水把我的眼睛漤得很疼也不敢用手去擦一下,我穿的短袖衣服和棉绸裤都被汗水泡湿,我们就这样一秒一秒的熬,一分一分的忍。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每次只有三分钟时间,还要爬上二楼,每次只得跑步去跑步回,由于泡湿的裤子和臀部肌肉粘在一起,一拉裤子,臀部肉皮就被拉掉一块,我的臀部又开始红肿化脓。一天早晨我的臀部右边一点不敢接触塑料凳,一接触就疼痛难忍,我只能靠左边坐军姿,臀部疼得我心里发慌,一阵阵的恶心,小腿在颤抖,最后我几乎要晕过去了,一直熬到中午上厕所,我叫功友汤云霞帮我看一下,她说已经红肿化脓了,便立即取下她戴牌的锁针,帮我把脓放掉,然后我回到集合场又坚持坐军姿。
由于恶警不许我们洗澡、洗衣服,天天只得穿这一身被汗水泡湿晾不干的衣服,我的身上长满了疥疮,全身恶痒难忍。与我臀部受伤同样严重的李凤其、王红霞、陶菊花等也在同样罚坐军姿。李坤容就这样变着花样惨无人性的折磨法轮功修炼者,我们就这样天天一秒秒,一分分的被煎熬着……。
然而皮肉的痛苦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意志,我的心境仍然是那样的美好、祥和,因为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的决心是永远坚不可摧的!
强行洗脑
七月中旬,国家司法局带上马三家的人来劳教所转化我们。早晨队长李坤容叫我去听转化,她感觉我一身衣服臭得难闻,便叫功友邢琛去给我拿了一件干净的衣服穿上,然后带我到中队管教科办公室,我、毛昆、罗长华、李凤其等被安排在那里听转化,我听见那个人胡言乱语一阵,便起身就走,这时其余的几位功友也起来走了。中队干事李军把我带回来一边走,一边劝我,叫我应该好好听,我说她全是乱说,她讲的东西我师父没有这样说过,我不会再去听。但第二天早上干事李军和队长李坤容又叫我去听。这次是在劳教所的小会议室里面,有空调,有水果、矿泉水及瓜子等很舒适,有二三十个大法学员在听,那个做“转化”的人有五十多岁。我举手起来说:“她没有说对一句大法中的内容,全部是邪说。”并给大家背我们师父是怎么说的:“同时在传法过程中,我们也讲出了做人的道理,也希望你们从学习班下去之后,如不能够按照大法修炼的人,最起码也能做一个好人,这样对我们社会是有益的。”(《转法轮》)在《佛性无漏》中,师父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她再也讲不下去了,便大叫起来:“叫你们的队长把这个人带出去,她是来捣乱的。”我便起身出去了。
下午恶警又叫几十个功友排好队去听转化,我在太阳坝被罚坐军姿。李军又来叫我去听转化,为了揭穿转化者的谎言我又去了。一進会议室,还是上午那个人在讲,她看见我便说:“不愿意听的人,可以离开。”我转身走出了会议室,还有几个功友也随我一起离开了。
等在会议室外面的队长李坤容,看见我又出来了便对我大发雷霆,吼道:“上午你去捣乱,下午又把人带出来。”我刚進中队大门,它便叫道:“民管会给我弄去罚。”于是民管会龙平又把我弄去禁闭室罚做下蹲(两手抱在头顶蹲下去再站起来,蹲完后站不稳,必须在小凳上趴一会儿才能慢慢的一拐一拐移动双腿)。它强迫我蹲下去,由于早晨我们全室炼功才被罚蹲了六百多次,两腿疼得蹲下去都很困难,我只得咬住牙一次一次往下蹲,一次一次的数出声来。我的汗水雨点般的从头发尖、脸颊上往下滴,我感到呼吸困难,心跳不知道有多快,虽然是七月份,汗水滴在地上一直未干。这一天我总共被罚做了一千多次下蹲,从此它们再也没有叫我去听马三家来的人的所谓转化。
晚上睡觉值班的民管会不停的用电瓶灯在每间寝室来回的照,我炼功被它们发现了。干事李佳蓉拿着一根狼牙棒气势汹汹的开门進来,边吼边用狼牙棒使劲的往我背上打,只听狼牙棒咚的一声从我背上弹起来。当时我受伤的臀部肌肉已腐烂,只能爬着睡觉,无法翻身,我告诉它,我的臀部有伤,不能打,它打完后气冲冲的出去了。
一天晚上,我炼功包夹大吵大嚷不让我炼,到了深夜民管会就罚我在走廊上做下蹲。在楼梯旁民管会人员值班处,我看到大法弟子陶菊花睡在地上。她告诉我,由于她不转化,队里的警察不准她回寝室睡觉,她已经在走廊上睡了几个晚上了。我被罚做下蹲,我的衣服全湿透,汗水象雨点一样的往下滴,罚完后我无法走路,就双手扶住走廊栏杆和菊花相互鼓励要坚信师父,决不转化。
我又被弄到二楼楼梯口旁边的寝室里坐军姿,由同寝室里的两个人包夹。寝室里有十四个人,轮番的骚扰我,白天上厕所都由她们跟着,不准我和坚定的大法弟子说话,甚至连点头也不准。我上厕所时看见坚定的功友还在集合场被罚坐军姿、晒太阳,我便竖起大拇指,鼓励他们要坚定,结果被包夹发现,报告队长后把我弄到办公室去骂了一顿,然后增加劳教期十五天。
我们每天从早到晚的坐军姿,我都静静的背法,一关关的挺过来。中队的所谓上大课,其实就是批斗会。在集合场上课,每次都要把坚定的大法弟子叫起来罚站、大骂。一天早晨刚上课,队长李坤容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善”字,叫我回答什么叫“善”,我说“善”就是对任何人都要好。“你给我闭嘴!”李坤容对我大骂道。骂我不转化就是不善,就不配说善,从早晨一直骂到中午。
二零零一年九月初,为了转化我,李军通知我的家人和朋友带着儿子来劳教所做我的所谓“转化工作”。中午,队长李坤容和干事李军带着我到管教科外面的坝子里,我的儿子、哥哥、嫂子和朋友早已等候在那里。由于我天天坐军姿晒太阳,身体瘦得皮包骨头,人都变形了,除眼角的几条皱纹睁着眼时被遮挡住没有晒黑外,手脸晒得象黑人一样,我的亲人看见我被折磨成这个样子,他们都伤心的哭泣。队长李坤容叫我站在亲人面前,大骂我不转化,叫我七岁的儿子抱着我的腰,儿子吓得赶快过来抱着我一动不动。送我家人来劳教所的驾驶员听见警察那样恶毒的骂我,赶快走得远远的站着。
我轻轻的松开儿子的小手低着头告诉他:“你乖一些,别怕,你要记住妈妈是好人,以后妈妈会回来带你的。”儿子没敢吱声,脸上淌满了泪水,轻轻的点了点头。我慢慢把儿子移开站直,队长李坤容的骂声仍然不绝于耳,儿子站在我旁边一直流着眼泪,他的两只小手在他带的钥匙环里转来转去,还不停的用小手擦眼泪,脸被摸脏了。就这样李坤容骂了我几十分钟,才叫李军把我带回中队去。
我的亲人看见我又被带走,哭得更伤心了,离开他们很远了,我回头,看见他们仍一动不动的望着我孱弱的身影,显得是那样的依依不舍。回到中队,我静静的想:是谁这样残忍,让我们骨肉分离;我真正的在做一个好人,却被非法关押,残酷迫害,为什么?我想起了警察张小芳经常骂我们的话:“你们炼法轮功就是反革命,就是要对你们专政!”其实,法轮功修炼者就是“真、善、忍”的修炼者,是一群在净土中修炼的大好人,没有罪!是的,上亿的大法弟子在江泽民的迫害下,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一夜之间都成了被专政的对象,而我们却只因为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坚持我们的信仰,就要被这样无端的迫害。
善良的人们,你们可否感受到我当时的心境:儿子三个月就没有了父亲,一直和我相依为命,六岁,相依为命的妈妈又被抓去坐牢,这对他幼小的心灵该有多大的伤害,然而在这种残酷的现实面前,在中国亿万的法轮功修炼者身上不知还有多少遭到象我和我儿子一样的不幸!
由于我不转化,它们又把我调到三楼厕所旁的寝室進一步迫害。每天除了本寝室的人外,还要安排中队其他的人来转化我。一天晚上室长张玲拉肚子,因为每天晚上睡觉门都是由民管会锁了的,是在寝室里解便,那天便桶拉满了,张玲叫民管会开门上厕所,张玲和民管会吸毒人员就吵起来了。第二天早晨集合时,张小芳就对我叫道:“周慧敏,你是修‘真、善、忍’的,你把昨天晚上吵架的内容说出来。”我说:“她们吵架的内容很多,时间很长我记不住。”而且我也不会去说这些。张小芳大发雷霆,叫我所在的三分队,几十个人针对我开会。我静静的坐在三分队车间里听着她们的发言。她们针对我的不转化,又進行了一场批斗会,一直开了一整天,我以一个修炼人的大忍之心,忍受着她们对我所進行的指责、讥讽。我看见我昔日的功友被洗脑后变成这样,心里非常难受。其他坚强不屈的功友有的已经分到吸毒队去了,進行强制劳动,我仍被留在七中队强行洗脑转化。张小芳不允许其他功友和我说话,不准我和任何功友打招呼,只能听来转化我的人对我的转化。最初和我在吸毒三中队的吴会珍由于她没放弃修炼,被两人包夹。一天上午她走在我的面前伸着舌头给我看,她的舌头裂开了大条大条的口子,我看了便心疼的问了一句:“你疼不疼。”结果被包夹们发现,说我跟吴会珍说话了,队长李坤容把我叫去办公室,当着中队警察的面又辱骂了我一通。走出办公室,我想起了师父的话:“一个修炼的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所以在历史上能修成圆满的才寥寥无几。”(《位置》)
关在黑屋里50多天妄图强行洗脑
包夹我的人已经陆续解教回家了,恶警又把我关在二楼厕所旁边的寝室里由室长来包夹我。寝室有十四人。我被关在寝室的里屋小间里,房间光线很暗,吃喝拉都在里面,不准走出小间半步。每天由两人一组包夹来转化我,队长张小芳还要安排其他寝室里的人来转化我,每天最多有七批人来给我做转化。所里、队里都同时加大了对我的转化力度,因为它们要提高转化率。管教科罗科长给我做转化,过几天罗科长又把我带到王所长办公室给我做转化。王所长说:“全所一千多人,我不可能找每个人去谈话,我们是重视你,我亲自来转化你。”我说:“王所长,我不转化,我从小就病魔缠身,在痛苦中,在我绝望之时,我得到了法轮大法,是我师父帮我净化了身体,净化了思想,净化了心灵,我感到修炼是那样的美好。炼功前,我的病是专家教授们都束手无策的,我的神经官能症一会儿是忧郁型,一会儿是躁动型……炼功后,一直没吃过一粒药,法轮功实在太好了!”王所长又说:“你不转化只有永远关在劳教所里……”最后我说:“假如今天你给我选择的是两条路,一条是转化,一条是上刑场,那么我就选择上刑场。”他无法转化我,就叫罗科长把我送回中队。
我被继续关在小间。又过了几天,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一行又来劳教所把我弄去三分队车间做转化。由于长时间关在小间,对外面的环境有些不适应,我感到阵阵发冷。但我很快调整好自己,在它们安排的地方坐下。两个摄像机在我旁边转来转去。王所长说:“今天的会只有科长和所长级别才有资格参加,中队干部都没有资格参加……”司法厅的副厅长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周慧敏,你决裂法轮功不要再炼了!”我就对他讲了法轮功祛病健身功效非常超常,讲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的巨大变化,讲我们的师父在教我们如何做一个好人,做好人应该没有错,应该允许、支持才是。我告诉他我永远都不会转化。它们不让我再说,便开始讲些诽谤、诬蔑我师父的话。我严肃的告诉它们:“请你们尊重我的师父,我不允许你们这样诬陷我的师父,即使上刑场,我也不转化!”我又重申了自己的信念,它们无奈,只好草草收场。
在集合场边缘站军姿
我在黑屋子里被关了五十多天,又被弄到楼下三分队车间,听人读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的文章。我不听,它们又把我和其他坚定的大法弟子陶菊花、王红霞等一起弄去罚站军姿。当时是二000年十一月底,天很冷,我们从早晨七点站到晚上十一点半,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都这样站着,我的脚肿得皮鞋都穿不進去了,只得穿上功友送给我的一双又长又大的布拖鞋。每天站得脚心象针扎一样,疼痛难忍,小腿肿得象大腿一样粗,手肿得象包子一样,拿筷子都不好使,就这样天天罚站,就连吃饭也不允许坐,端在手上站着吃。我背着师父的经文《真修》:“你们知道吗?佛为度你们曾经在常人中要饭,我今天又开大门传大法度你们,我没有因为遭了无数的罪而觉得苦,而你们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是的,我作为一个大法的真修弟子,认识到了佛法的真理,人想用什么手段来改变我都是徒劳的。
一月十三日,中队开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的会,由于每次这种邪恶的会坚定的大法弟子都要起来维护大法,张小芳便叫护卫队来维护会场。早晨我仍在集合场边缘罚站军姿,护卫队队长杨小平叫我去听诽谤会,我不去,它就拖我去听,我还是不去,其他几个同我一起被罚站的大法弟子也不去听。张小芳和管教廖小玲在我的前面同时猛踢我的腿,护卫队队长杨小平同时又在背后狠狠的踢我的腿,我仍然没有坐下去。杨小平拉着我的棉袄往外一摔,纽扣被扯掉,棉袄被撕破,我被摔在地上滑了很远,我的羊毛外裤也被磨破,然后它将我双手反铐在背后,拖过去按在小塑料凳子上叫两人一直按着我,强制我坐在凳子上听诽谤会。旁边已被强行洗脑的功友看见它们这样残酷的迫害我都哭了。
我就这样一直被罚站军姿,直到二00一年春节。我们由罚站军姿改成坐军姿。二00一年大年三十、初一,天下着小雨,我们仍然被罚坐在集合场淋雨。头发尖都在滴水,除了大腿放手的地方是干的以外,其余都是湿透了。在雨雾朦胧中,我静静的想,春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是合家欢聚的日子,而此时的我却因坚持自己的信仰,被非法剥夺了作为一个华夏儿女应该享有的快乐和权利,我的亲人此刻该是多痛苦,我可怜的儿子又是多么地想他的妈妈啊!因为每年这个时候我都会与他一起放烟花庆祝这无比美好快乐的节日。亲人们,擦干眼泪吧,同我一起抵制这场没有人性的迫害!此刻的我也为自己能这在邪恶的环境中捍卫宇宙大法而倍感自豪。虽然一、二月份是最冷的日子,我却没有半点凉意。由于没有衣服换,晚上睡觉只好用自己的体温把湿衣服温干,明天好继续穿上。
电警棍酷刑
二零零一年五月,所里管教科的人拿了一张大红布放在中队乒乓台上叫签名。红布上面写着针对我们大法的诽谤宣传。张文红、张世清、张凤清等几位功友站出来证实大法,队长秦文霞、干事胡容就把她们一个一个的分别拖進办公室,把门关上用电棍电。当时我坐在最边上的那排,正好对着办公室的门。电警棍发出恶毒刺耳的声音,使我再也无法静心背法,好象电棍是电在我身上一样。我的心难受极了。张凤清被电了几十分钟才放出来,接着又把张文红拉進去电。我想我们都是大法弟子,我应该和她们站在一起,于是我就盘腿打坐。坐在我后面的吴慧珍功友也开始盘腿打坐。这时民管会的人便立即冲过来,把我的腿扳下来,我站起来直接去办公室,此时张文红被电完出来了,我正准备進去,队长秦文霞拉住我,先把吴会珍拖進去又电几十分钟。吴会珍被电完出来,我直接走進办公室。当时队长张小芳从外面回来刚進中队大门,干事胡容和秦文霞同时告诉张小芳,说周慧敏又打坐了,张小芳一進办公室,见到我就说:“你打坐,今天我要你打坐!”急忙从墙上取下一支电棍(办公室墙上挂着一排电棍、一排狼牙棒、一排手铐)对着我的脸开始电,我上前一步站得端端正正一动不动,让它电,心里在背着经文《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惜留……”而电棍却没有声音,它又把电源打开,对着我的下颚又电了一下,电警棍仍然没有声音,它又对着我穿着短袖的大臂电了一下,仍然没有声音,张小芳气得把电棍往办公桌上一甩,就这样才停止了对其他大法弟子的电警棍酷刑。
转到八中队
二00一年六月二十日我被转到八中队,张小芳指使民管会的人对我已打好包的衣服、被子乱翻,把我的棉被、衣服都捏了一遍,收走了我的“法轮章”,张小芳发出得意的怪笑。我心想:大法早已装進了我的脑子里,装在了我的心里,那是你永远也搜不到的,干这些愚蠢的坏事多可悲呀!
到了八中队,干事又指使民管会的人把我的衣服、被子和所有的东西都捏了一遍,叫一个被强制洗脑后的人对我实行二十四小时包夹。
一天,我吃完中午饭在寝室外面的走廊上被迫做奴役劳动夹猪毛(黑毛里选白毛),看见七中队坚定的大法弟子又在集合场的烈日下被罚坐军姿,我向她们招手点头微笑了一下,被七中队民管会人员发现告到队长秦文霞那里去了。下午秦文霞到八中队和八中队的曹队长以及一位干事把我叫到办公室骂我,一直骂至中队的全部劳教人员吃完晚饭。
二00一年八月八日我又被转到九中队。那里的“民管会”全部都是吸毒人员组成,那里坚强不屈的大法弟子多一些,几乎每一个寝室都有。我所在的寝室里有一个攀枝花的大法弟子燕宝平,很坚定。我们两人都被包夹。自从二000年起国家司法局的人和马三家的人来劳教所后,就一直不准我与别的大法弟子说话,二十四小时被包夹。我和功友燕宝平连相互点头都不允许,每天包夹人员都把我和她隔得远远的,连晚上睡觉,包夹人员都坐在我们的床边,通宵守着。但是我和宝平彼此都感到非常的亲切,晚上睡在床上,其他的人要转化我们,我们俩人都会一齐抵制并帮助她们不准乱说。恶警白天就把我们弄下楼去,以分队为主坐在集合场,吸毒人员读诽谤我师父和大法的东西,坚定的大法弟子谁也不听它们的,各自都静静的背着法。
不做体操
我不做广播操,我得炼法轮功。一天下午我看见集合场60多岁的老功友谭光荣被拖着、推着围着集合场边缘跑。八月份天很热,她被拖着、推着跑了很长时间了,我的心很难受。正在这时,干事李佳容到寝室来问我:“周慧敏,明天做不做操?”我说:“不做!”她说:“你做不来我找人教你做。”我说:“我做得来,我不做。”她连问几遍,我做不做,我都坚定的回答:“不做!”这时她就叫吸毒人员把我拖下楼去,并把每间寝室的门都由吸毒人员民管会守着,不准任何人出来看。在中队办公室外面的阴沟处集合场旁边,她叫几个民管会吸毒人员围着我叫我做操,我不做,它们就把我的头往下压,靠近膝盖处,并把我的双臂反扭往后抬,我挣脱它们就地盘腿打坐,这时李佳容大叫:“你敢炼功!”就叫吸毒人员来围着我乱踩乱踢。
它们把我踢翻在地,又踢了很长时间,李佳容和另外一位干事叫吸毒人员把我拖進办公室旁边的一间空屋子,然后把我的四肢全部拉直,两腿张开,并站在我腿上,肚子上使劲乱踩,折磨我很长时间,然后李佳容又大吼:“把绳子拿来!”这时曹队长(原八中队调往九中队的)進来了,叫他们别忙绑,曹队长说要和我好好谈谈,当时我没有识别到它的假善,它叫我起来,它跟我讲条件,只要我明天做操,它就不惩罚其他不做操的大法弟子,如果明天我不做操,她就要把其他大法弟子弄来惩罚。当时谭光荣功友跑不动了,被拖着跑,推着跑的情景让我阵阵心痛,想到还有年龄大的老功友可能难以承受它们的残酷折磨,我就同意了曹队长的条件。第二天、第三天我便做了两天操。下午在寝室里,我突然听到被洗脑的人在读劳教所写的已在全国发行的一些东西,说我们用做操代替炼法轮功,我马上悟到:我做操是错的,我不应该妥协,我应该和功友一起共同抵制做操才对。第二天早晨在集合场做早操时我便又站着一动不动。
就这样过了两天,通知我收拾东西,曹队长把我带到了管教科,我才知道我要回家了。
我终于破除了邪恶的非法关押迫害,堂堂正正的回家了,这天是二00一年八月三十日。但此时我已被非法超期关押了整整七个月,在楠木寺这个邪恶的魔窟里总共被关了一年零七个月。此时此刻回想起劳教所李军曾对我说:“周慧敏,你不转化就只有死在劳教所里,一辈子都别想出去,我退休了还有我的女儿和孙辈,你永远也把牢坐不穿。”可是每次背到师父的经文《警言》:“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每每此时我总感到佛法的威力无边 ,无所不能,深信我一定能战胜邪恶,获得自由。车子缓缓开出楠木寺女子劳教所的大门,我又一次深切的体悟了佛法威力在我身上的再现。
三十四天的毒打、酷刑
二00一年十月十一日我和朱银芳(现已被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迫害致死)、赵相容(她们是新疆人,也刚从新疆劳教所释放回来)切磋,我们都觉得应该堂堂正正的去炼功,让世人知道大法好。十二日早晨我们挂上“法轮大法”的横幅,又在昨天炼功的地方炼功、背“论语”。一个便衣警察来拖我们的横幅,被我止住了,我拿回了横幅,同时它又打手机报警,我们及时发正念制止它,背完“论语”后,安全的离开了。
二00一年十月十三日我和陶菊花、朱银芳、赵相容又带上横幅去成都天府广场准备炼功,到了广场才早晨七点多钟,广场上人还不多,我们便先发正念。这时两列武警向我们冲来,把我们绑架到主席像的背后,不一会儿就开来了两辆面包车,把我们绑架到成都西御河派出所,并把我们四个分别弄到四个办公室,叫我们报姓名、住址,我们谁也没有报,只是告诉他们,我们是大法弟子,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
我坐在警察办公室没有事,就发正念、背经文。最后来了一个警察把我拖到值班室外面的院子对面一排破房子旁边。朱银芳和赵相容已被警察反铐在大树旁,我和陶菊花便盘上腿,我们四个大法弟子又开始集体背经文,旁边有几个年轻的男便衣在监视着我们。
中午,过来几个警察指使便衣人员把我们拖進两辆车开出成都市送往龙泉驿看守所。我们被拖進一排低矮的房子外面,这时女警察就开始来搜身,我不让她搜。一会又来两个男警察提来了脚镣、手铐,它们强行给我铐上脚镣、手铐,然后脱掉了我的皮带,拉着手铐把我强行拖上二楼的女监一室。“我没有罪,不应该戴这些东西!”我对它们抗议道。便把手铐脱下来丢了,我也不和其他犯人一起端坐学刑法,因为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没有罪,我叫同监室的大法弟子李小军、陈碧华等同我一起背经文。
晚饭后,由魏所长带队来了四、五个男警察,把我拖下水泥铺板,当时我还戴着脚镣的,它们把我拖出监室铁门,甩在走廊上。魏所长对我头部首先猛击几拳,把我打翻在地,其他几个警察围着我猛踢。魏又去打来冷水对着我的头,一次又一次的泼,我的衣服都湿透了,然后又强制给我铐上手铐,拖回监室甩在过道上锁上门走了。
由于我戴着脚镣手铐,功友也无法给我换湿衣服。晚上功友李小军给我盖上棉被和我睡在一起帮我把湿衣服温干。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又来了七、八个警察,李小军说:“你们这些警察太过分了,把周慧敏的脸都打变形了!”她话音未落,警察便又冲上来把我盖的棉絮扯烂扔了,两、三个警察冲上水泥板,又开始对我進行拳打脚踢。它们又强行给李小军戴上手铐。
十四日中午我又把手铐脱下来丢了,召集(即牢头)许晴又报告了干事。不一会又来了几个男警察把我甩倒在水泥铺板上拳打脚踢,一个警察对着我的太阳穴猛击两拳,当时我的左眼被打得直冒金光,整个大脑发胀,人几乎都要晕过去了。至今我的左眼还经常出现那种被打得冒光的症状。最后警察又强行给我戴上“龙抱柱”(注:双手和腿铐在一起,不能站立行走,只能蹲在地上慢慢移动)。早晨查监发现我在念正法口诀,这时又来了七、八个警察打我。功友李小军告诉陈功友她们,说不允许它们再把小周拖出去打,要保护功友。于是警察拖我时她们三个功友死死的抱住我,不让警察拖走我。这七、八个警察全部冲上来打我们四个大法弟子,它们把李小军先拖出去,然后又把我拖出去,甩在走廊上。它们把我拖过长长的走廊甩在办公室的地上,我闭着眼睛立掌发正念,一会儿它们又把我拖回走廊上,一个男警察摸出他包里的卫生纸把我被打出的鼻血擦掉,又把我拖回监室甩在过道上。此时功友们全部被戴上手铐,只得由几个犯人把我抬上水泥铺板。中午六十多岁的肖功友因手铐铐得太紧,疼得晕过去了,突然从铺板倒在过道上,下午她苏醒过来后,就把她释放了。
提 审
十月中旬的一天早晨监室门打开了,一个男警察气势汹汹的叫犯人把我拖出去,把“龙抱柱”改为脚手分开铐,说要提审我。我不去,这个警察就拉着我的手铐把我往楼下拖,经过长长的走廊脚镣卡在我的脚颈骨头上疼痛难忍,就这样一直把我拖到一间低矮的屋子里,一个年轻的警察早已等候在那里,因为我当时的脸是被打变形的,他见我便说:“看你这样,就象个死刑犯。”我说:“只是我修炼法轮功做好人,就把我当成死刑犯来对待。”他叫我坐下,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大法弟子。”他又问:“你家住哪里,我说我除了告诉你法轮大法好之外,什么都不会告诉你。”他说:“我实际上也是来完成任务,拿回去交差,看你在这里弄成这样。”我说:“几天前你们送我来时,我都是好好的,现在被毒打折磨成这样,难道监狱就是这样知法犯法吗?也许你不敢告诉我江泽民给你们指示:对法轮功实行“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对吧?打我的那个姓唐的狱医说过:“江泽民给了我很多钱,就是叫我来打你。”但是我告诉你,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而且我也真的在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更好的人,做好人怎么会有罪呢?江氏集团打压法轮功两年多了,你们抓了多少法轮功学员,你们有没有见到一个法轮功学员是吃、喝、嫖、赌、偷、抢、杀人的,没有吧?对这样的好人被非法绑架折磨成这个样子,象你所说的就象个死刑犯,而折磨的原因仅仅因为她信仰“真、善、忍”,想做个好人,这让人怎么理解啊!我给你讲了这么多,你觉得我应该呆在这里天天受这样的酷刑折磨吗?真的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法轮功修炼者,所以我希望你们释放我。”他沉默不语,最后收拾好东西,起身走了。警察又将我拖回监室,我的两个脚颈被镣铐卡伤的地方疼得难忍。
集体脱铐
又过了几天的一个早晨,我听见监室的铁门开了,传来铁镣、铁锤的撞击声和拖地声,我看见功友赵相容拖着沉重的铁锤、铁镣一步一步的向我坐的方向移动过来。她脚戴三副铁镣,双手还反铐在背后,其中两副都是吊了重铁锤的脚镣,她的小腿又粗又短,有两副铁镣的环都扣在肉里了,她的小腿很长一段肉皮都变黑了,磨出了老茧,当时我只戴了一副带铁锤的铁镣,腿移动一下,铁镣的铁环卡在骨头上,钻心的痛,我不知功友赵相容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朱银芳、陶菊花也拖着脚镣、铐着背铐来到了我的监室,我们功友切磋:我们是炼功人,不能被他们这样铐着,应该脱铐炼功。于是,我们通过“随机下走”把背铐通过臀部,往脚下移,然后把它移到了前面,我们就发正念脱铐。朱银芳的手由于被反铐在背后已经十几天了,双背都僵硬了,我们只得帮助她从背后直接把手铐取掉,她的手肿得很厉害。脱铐时她手背一片厚厚的肉皮被手铐刮掉了,我们都互相帮助发正念脱铐,结果把铐子全部都脱掉了,这样我们就可以炼功了。
由于我们脱铐被招集报告了警察,每天都要来七、八个警察打我们,然后踩着我们的头、身子、腿,反扭着我们的手强行给我们戴上铐子。每次警察冲上铺板来打我们,把所有的犯人吓得在一瞬间贴着墙边缩成一团,他们害怕极了。有个犯人是个小女孩经常来帮我们理顺被警察扯乱的头发,她流着泪对我说:“我看它们打你们那么狠毒,我只有偷偷的哭,怕它们打我。”我说:“你还这么善良,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她点点头。是的,江氏团伙是想通过这种镇压来消灭法轮功,然而毒打酷刑对法轮功真修者是没有用的,我们是“真、善、忍”的修炼者,也是“真、善、忍”宇宙大法的维护者,这是它们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一天早晨十几个警察又提来几副脚镣手铐,冲上铺板准备把我们连起来铐上,我们不让警察这样铐,它们就抓住我们的头发把我们的双臂反扭在背后,戴上板铐,然后在我们每两个大法弟子之间,又加一副带铁锤的脚镣和一副手铐把我们全部连铐在一起。加上自身戴的脚镣手铐,我们七个人总共戴了脚镣15付,手铐13付(其中赵相容一个人就被戴了三付脚镣)。我们无法上厕所,无法吃饭,连移动一下都实在太难了,没有办法,我们只有集体不吃不喝。
五天后警察才给我们取下了连铐。我们每人仍然戴了一副带铁锤的脚镣和手铐,我们还是坚持每天脱铐炼功。警察把我们的手铐由最初露在外面的六个齿增加到十一齿,也就是铐得越来越紧,手铐已陷進肉里很深,我们的手肿得象包子一样。一天脱铐时,我的右手背边缘靠小指处被手铐划掉了一大块厚厚的肉皮,露出一片红红的带血水的烂肉,第二天早晨它们又来强行给我们戴铐时,一个姓杜的女警察把我划破的手拿起来看了一看说:“周慧敏呀!”然后放下我的手就离去了。是啊!在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血腥镇压下,想炼功就要受到如此的迫害!
“龙抱柱”酷刑
即使已对我施了重刑,它们还不甘心,最后把我们全部铐成“龙抱柱”。被戴上“龙抱柱”后打我们最多的是姓唐的狱医,查监时它总走在最前面。这天早上,相容在念正法口诀,它冲上铺板对着坐在铺板上的赵相容的脸,用皮鞋乱踢,赵相容的头被踢得扭过去,她转过来时又被踢过去,就这样反复的踢了很久,相容的嘴被踢破了。目睹它们的暴行,我反复背诵着师父的经文《秋风凉》:“邪恶之徒慢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相容中午吃饭都无法张嘴,满脸踢成紫块。相容和李文怡还被警察用一种象苍蝇拍一样的刑具毒打,是用厚铁板钻上6毫米左右的小孔制成的刑具,抽打大腿和臀部,被抽打处的肌肉全部成紫黑色,并且都是小疙瘩,很长时间都无法散掉,恶痒恶痛。
经过三十四天的毒打和酷刑折磨后,它们才给我们解开了“龙抱柱”和脚镣、手铐。
(待续)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5/5/7/604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