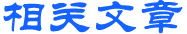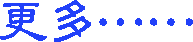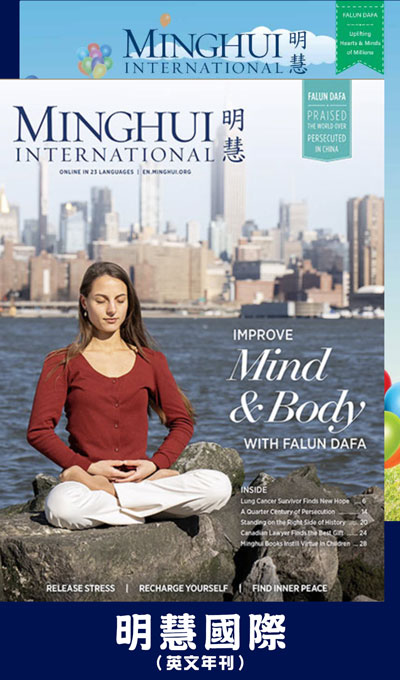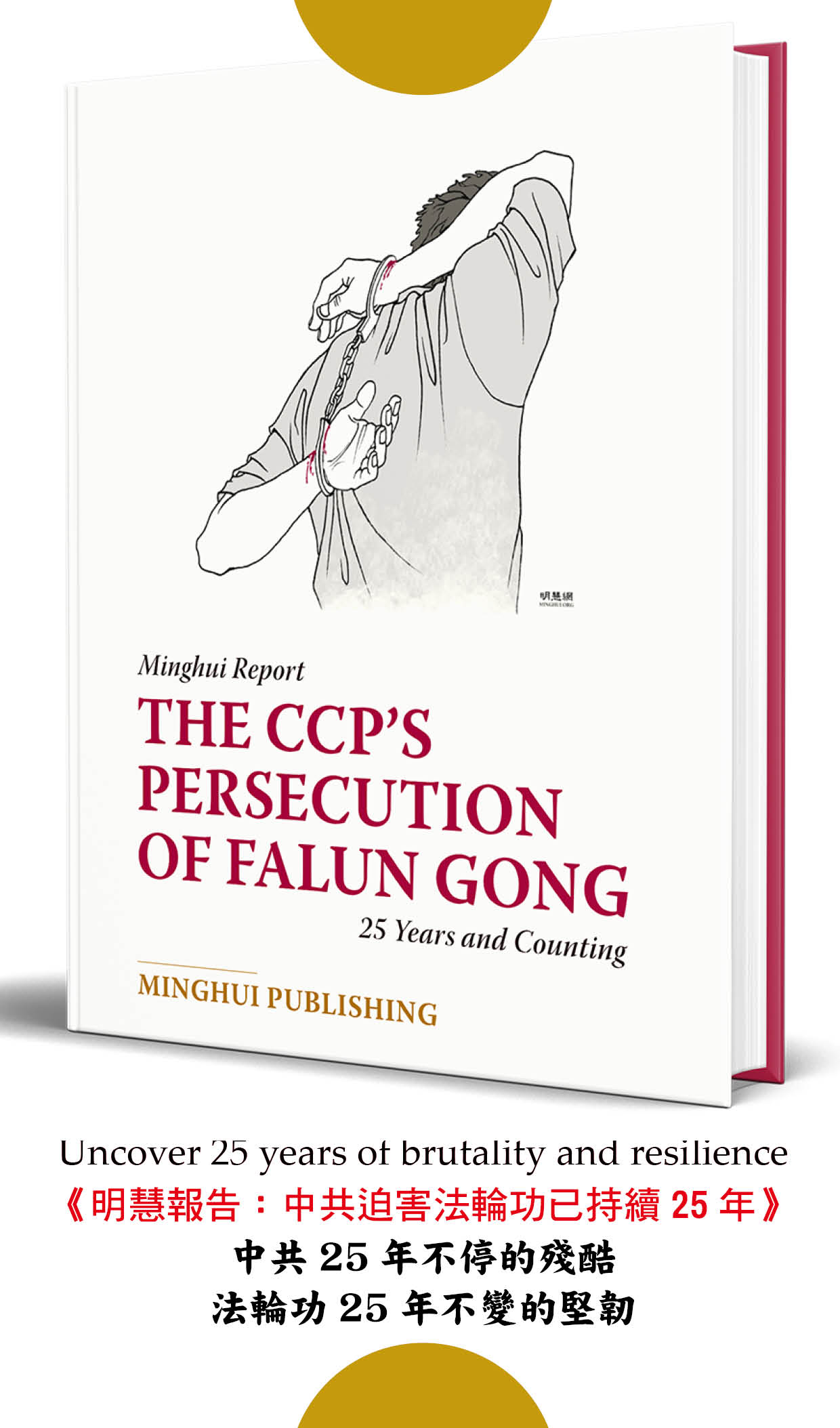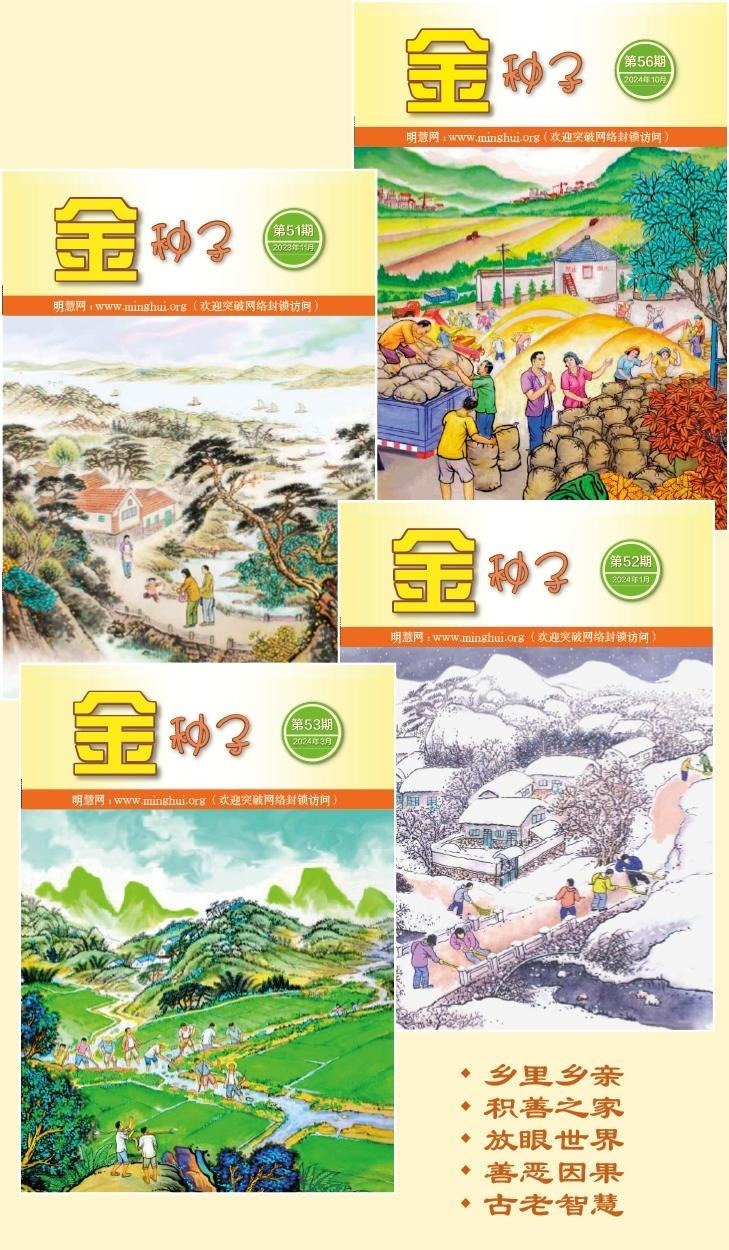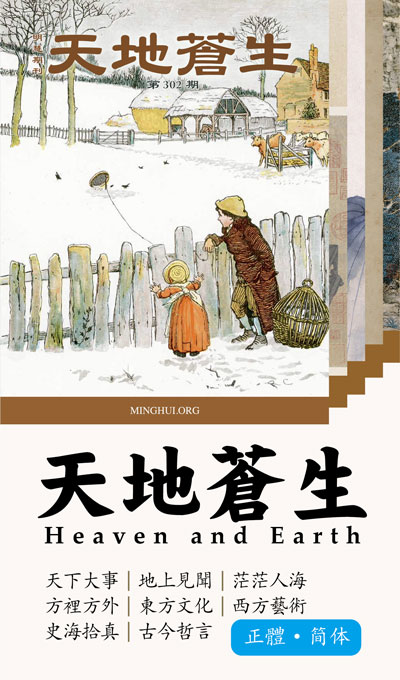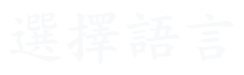我闯出马三家集中营的历程(二)
至十七号,我们被当地警察带回,在当地公安局政保科,他们问我还去不去上访,我说:“只要师父和大法蒙冤一天,我就一天不停止上访”。当晚我就被送到了拘留所,在拘留所呆了十二天,十月三十一号,我被非法判教养三年,被送到了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院。在这个臭名昭著的教养院里,长期受着摧残和迫害。
十月三十一号,邪恶的辽宁省不法官员统一命令,全省第一批被非法判教养的女大法弟子全部在三十一号前送到马三家。来马三家前,我只知道有监狱,根本不懂还有教养院,到了马三家,才知道原来人间还有这么苦的地方,人间还有坏到如此可怕程度的人。在这人间的地狱里,我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三十一号晚上,我们被送到女二所,所长苏境,大队长绍丽,队长是王小枫,都是恶人榜上多次提到的凶犯。十一月十四号这天,马三家下了第一场大雪,望着窗外的大雪,我感慨万千,因为这一天是我的生日,可这天晚上,我被恶警王小枫和陆跃芹毒打了一顿。这天晚上九点,因为炼功,我被四防连心〈鞍山吸毒犯人〉双手背扣铐在厕所的水管上,过了一会,恶警王小枫进来了,她揪住我的头发,用力将我的头顶在铁管子上,嘴不停地骂着,边骂边打我嘴巴,不知打了多少下,打得我只感到天晕地旋。这时陆跃芹进来了,她和王小枫让连心把我带办公室去,连心不用钥匙给我打开手铐,而是硬把我的手从手铐里往外拽,拽出后手都划破了。到办公室后,王小枫和陆跃芹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电棍,一齐电我,看着王小枫那狰狞的面孔、凶残的丑态,我真的不相信这也是一个女人,面对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她怎可能是一个温柔的妻子,一个慈祥的母亲?第二天,王小枫逼我写个保证以后不准炼功,我没有写,我说我保证不了。过几天我买了纸笔,写了四份材料,给江XX、朱镕基、还有我家乡的市委书记、还有省劳教局领导各一封,申诉师父和大法的冤屈,给我教养是错的。为迎接香港回归,王小枫让我们写稿,我就写了一首散文诗,抒发我对师父的怀念和由于迫害而使我修炼之路变得如此的艰辛。
后来恶警们把认为不太好对付的都送到女一所,十二月二十二号这天,我和许多功友被送到了女一所,我被分到了一大队的二分队,已经有好多功友早已来到了这里,我又见到了她们。在这里,每天被迫从事超负荷的体力劳动,每天工作时间长达十五至十六小时。而且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有一个包夹看着,吃的是玉米面饼子,给点菜汤,有时是玉米面粥,再给一点咸菜。因为长期不允许与家人接见,换季时,没有衣服换,天气很冷了,我们还穿不上棉衣,有时家人来看我们,因为不让家人见我们,家人就把给我们拿来的钱交给教养院的人,但我们却有很多人收不到钱,不给我们。我被送到一所后,家人不知道我在哪,到二所去看我,二所给一所打了电话,大队长把我叫去,问我想不想见家人,我说想见,她说那得写个不炼保证,我说我绝不可能写保证的,她说那就不能见了。就这样爸爸在繁忙的工作中,为了不耽误工作,利用星期天千千迢迢地来看我,却失望地回去了,留了二百元钱,让他们交给我,直到我走出教养院,我也没见到钱。
因为没有钱,我们连洗发精都舍不得买,用洗衣粉洗头发,舍不得买卫生巾,就用卫生纸代替卫生巾,因为卫生纸比较便宜。因为长期不让接见,到后来,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钱了,普教解教后扔下的衣服和鞋,我们拣回来洗干净后凑合穿,也顾不了体面了。马三家教养院想用不允许和亲人见面的卑鄙手段,在精神上折磨我们,在经济上拖垮我们,逼我们放弃修炼,但这一切难不倒我们这些师父的真正弟子,我们互相帮助,一人有钱大家用,哪怕是一袋方便面,也得十几个人分着吃,东西少如果只够每人吃一口,那就每人吃一口,也得都吃到。就在这样吃不饱穿不暖的恶劣环境里,还得每天早晨六点就出工干活,晚上十一、二点收工,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马三家的冬天格外地寒冷,大雪一场接着一场,由于零下二三十度的低温下,我们都用冷水,而见不到一滴热水,我们的手都冻裂了,手上又宽又长的大口子,还得完成超负荷的劳动任务,手上的口子经常出血。有的脸也被风吹裂了,有的还没有棉鞋穿。来马三家前,我从未干过体力活,做衣服更是一窍不通,她们就让我干零活,经常遭到普教的辱骂。后来,让我上机台,刚开始,我非常害怕干不好,也得撑着干,经常地加班加点。顶着星星出工,顶着星星收工,我们这样痛苦地过着每一天,艰难地熬着,但是,无论再苦再难,每当我想起师父,都有一种莫大的安慰,感到一种巨大的力量,在支撑着我。我深深地想念着师父,一想起师父,就泪流满面。
二零零零年的一月份,队长跟我们说,二所那边的人写保证不炼了,“转化”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转化”这个词,但我根本不相信。可是,没过几天,从二所就调过来了一批人,我们分队也分来了,而且其中就有在二所时,就与我在一个分队呆过的,晚上打饭时,我们见了面,一见面她就对我说,她“转化”了,保证都写了,现在正写揭批。我愕然了,难道队长说的是真的,我就怒斥她:“你揭批谁!你揭批什么!”她看我生气的样子,就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以后慢慢跟你说,你就明白了。”我又说:“不要跟我说!”从这一刻起,我心情好沉重,好难过,怒她们对师父和大法的侮辱,怜其她们的可悲。人类的语言何其苍白,用尽人类所有的词汇,都无法描绘我们师父有多伟大,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我们倾其自己的一切,都无法报答师父,可她们却要反过来揭批师父,令人痛心之至。
她们来到一所的目的是想“转化”我们。我们先过来的这些人,就商量想办法让她们清醒过来,而且加强背法,不受她们的影响。所以我们分队只有几个人受她们影响,大部份都没受影响。但这期间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有一个阜新来的学员,四十八岁,由于无法承受精神和肉体上的高压,突然出现精神病状态,被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纵,所以教养院就以此为例,攻击师父,攻击大法,可我们中又没有人与她是一个市来的,没有人了解她的过去,没有充份的证据澄清,给大法造成了很大影响,本来在我们的影响下,有好多普教已得法,由于她的影响,加上这些邪悟的人影响,她们不敢学了。后来,她的丈夫来看她,说她是有二十多年精神病史的精神病患者,师父在法中明确提出禁止精神病患者学法,这时才澄清,但她造成的影响却难以挽回。
二零零零年的三月份,教养院为了让我们放弃修炼,专门成立了一个分队迫害我们,我们一大队的三分队是这个专门迫害我们的分队,队长是周谦。这时又不断地从二所调邪悟的人过来对付我们这些坚定的,但只要是没彻底邪悟,还有一线希望醒悟的,我们就努力使她们悟回来,在我们的努力下,真有醒悟的。这时马三家放了第一批犹大,开兑现大会,看着这些可悲的犹大,我真为她们难过。会后,队长让我们写体会,我就写了一篇揭穿犹大谎言的洪法材料,每一次思想汇报,我都把她变成向世人洪法和讲清真相的机会。以前,我曾写过一份长达七页的洪法材料,用真诚和善心去启悟队长们的良知,告诉她们真相。自焚事件后我又写了一份材料,以揭穿邪恶谎言。
到二零零零年的六月份,邪恶开始向我们坚定的大法弟子下手了。指导员顾全艺,队长周谦把我们集聚一起,给我们开会,说上级指示,必须全部“转化”,不“转化”的,就采取强制措施,强制”转化” 。这时不让我们出工干活了,把我们与”转化”的分开。我们每天起床后就开始被迫坐小板凳,有的在走廊里罚蹲、罚站,每天至夜里十二点,其间还要邪悟的犹大找我们谈,谈完后,犹大就向队长汇报,看这个人有缝,然后就体罚,再用电棍电。这些犹大们就忙起来了,为了讨好队长,为了早一天回家,用自己以前的功友难以承受的肉体和精神折磨作为代价,给自己减期,谁卖力,谁对我们狠,谁靠近队长谁减期就多,就能早回家,但嘴里却冠冕堂皇地说为我们好,来掩盖自己的丑行。坐了几天板凳后,一天,一个犹大找我,说要和我谈谈,我说你想与我谈什么,你想与我谈法,我不与你谈,你都不炼了,你还谈什么法,你要是说点常人的家常,我可以跟你说。她说那你认为上北京上访对吗?我说上北京上访,永远都没有错,如果教养院放我出去,我连家都不回,直接去北京,为师父和大法鸣冤,她说你可真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所以一直没有动我。
但陆续有好多功友被恶警告知,哪一天挨电击。一天我们正在坐板凳,而犹大们非常逍遥,非常自由,她们在床上,怎么舒服怎么呆,这时,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伴随着电棍的噼啪声,当时我没有辨别出这喊声是谁,我的心揪紧了,我看了看周围的功友,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沉重,我意识到这一定是我们中的一个,因为有几个功友已与我们分离了,让她们与犹大们在一起。电击声持续了好长时间,一直不停,最后终于停止了。晚上,我到库房取行李时,我看到我的功友林燕,双手背铐在铁管上,只看她一眼,我的心已疼痛到了极点,可林燕为了安慰我们,忍着身心的巨创和痛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笑一笑,从此,林燕就被犹大们监控着,不让她与我们有任何接触。接着刘凤梅又被带到了办公室,这时的刘凤梅已在走廊里罚站罚蹲了几天了,当时我与刘凤梅睡一个床,到了晚上十二点,我们睡觉了,可刘凤梅迟迟不回来。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我睡着了,早晨还没等到起床时间,我因为床摇动而醒了,我发现是四防让刘凤梅起床,是想在我们起床前把她带走,不让我们知道她的情况,几天后,刘凤梅终于又回到我们中,可她却满身是伤,手上、嘴上的大泡还没消,恶警周谦,还有大队长王艳平,一天中就电了她好几次,刘凤梅始终不屈服,他们又用一种铁线〈是一种刑具,不知叫什么名〉抽打她,但都没有动摇刘凤梅对大法的坚定。这时,面对邪恶的疯狂,我们没有一丝的动摇,因为我们这时住在一起,我们就利用休息时间加强学法,会背法的就背,大家听。当我们刚到教养院,外面功友曾把新加坡讲法中的一段,写在一块白布上,送到里面,我就把法背了下来,经常背给功友们听,还有《我的一点感想》等经文。
这时我们听违心妥协的人(她们是承受不住酷刑,心里知道”转化”错)说,美国有个法轮大法宣传节目(其实就是明慧网站),我们这二十二个,都是九九年第一批进教养院的,对外面情况不了解,知道我们国外同修都在积极洪法,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我们想我们应该写下遗书,揭露我们所遭受的迫害,让国外的同修把邪恶的丑行公布给世界,因为我们随时都有被邪恶夺去生命的危险,如果不写下遗书,我们所遭受的一切就没人知道了。这时,一个违心妥协的人对我说,”转化”吧,要不一定挨打呀,你能挺得住吗?我说,也许我修的不好,我的承受力有限,我也许承受不住,但我宁可死也不会妥协,……我决不自杀,决不“转化”。她说,值得吗?我说,为大法而死,我死而无憾。
当我们这二十二个人心都坚定到这种程度时,邪恶怎么打怎么电怎么罚都不能动摇我们时,他们也无能为力了。强制”转化”就暂停了,又让我们出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