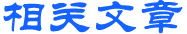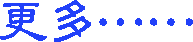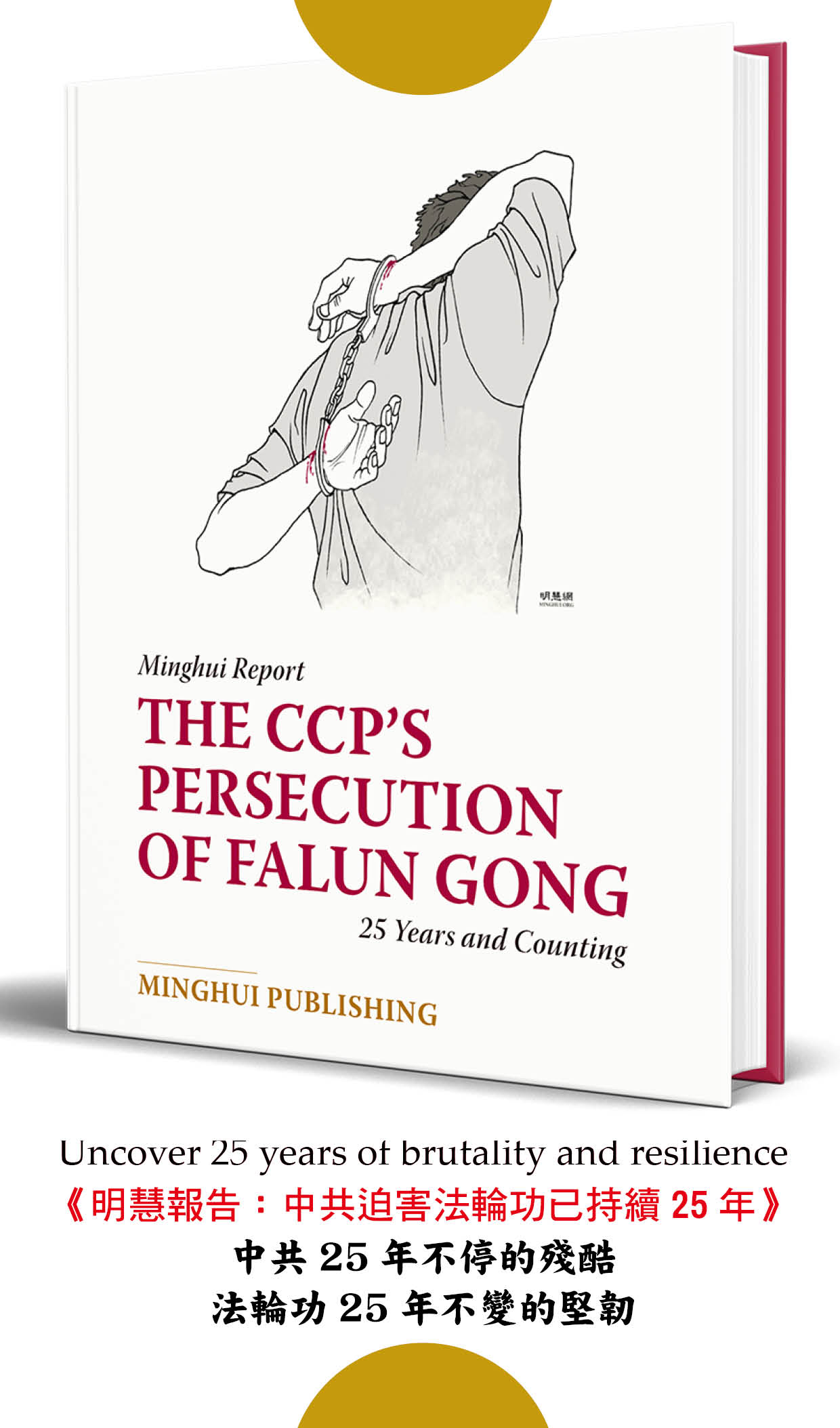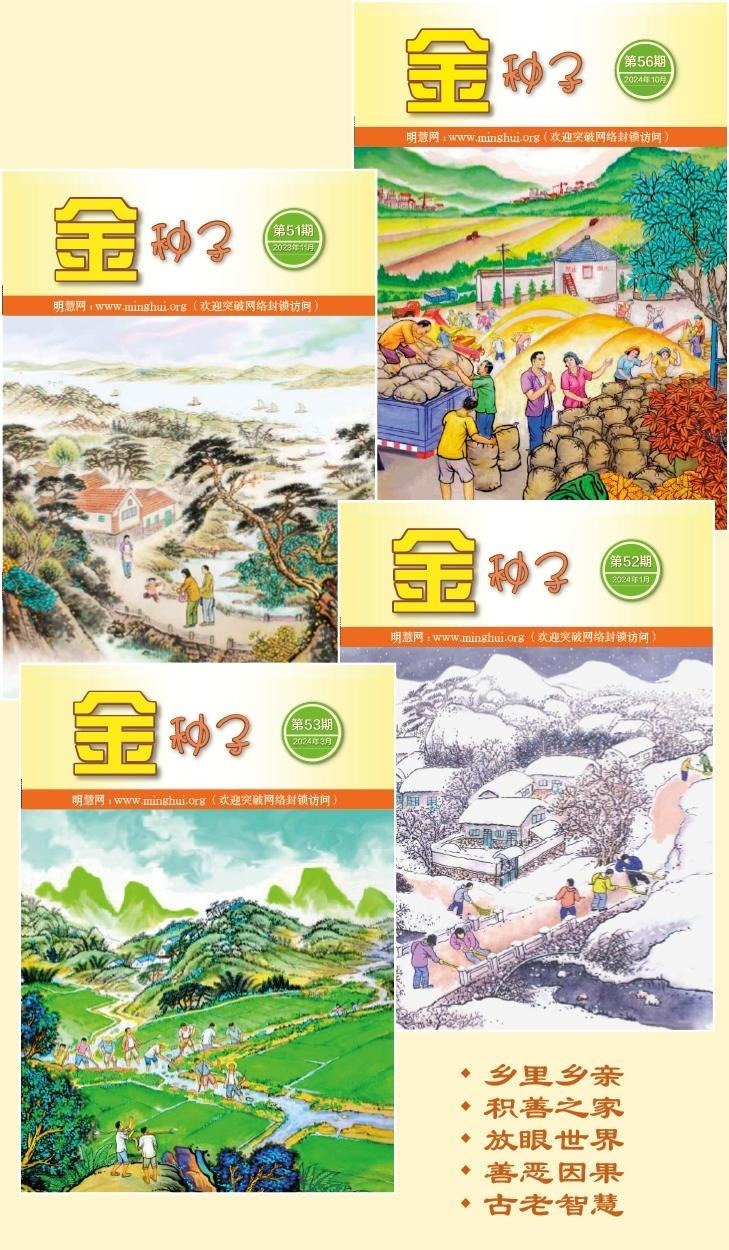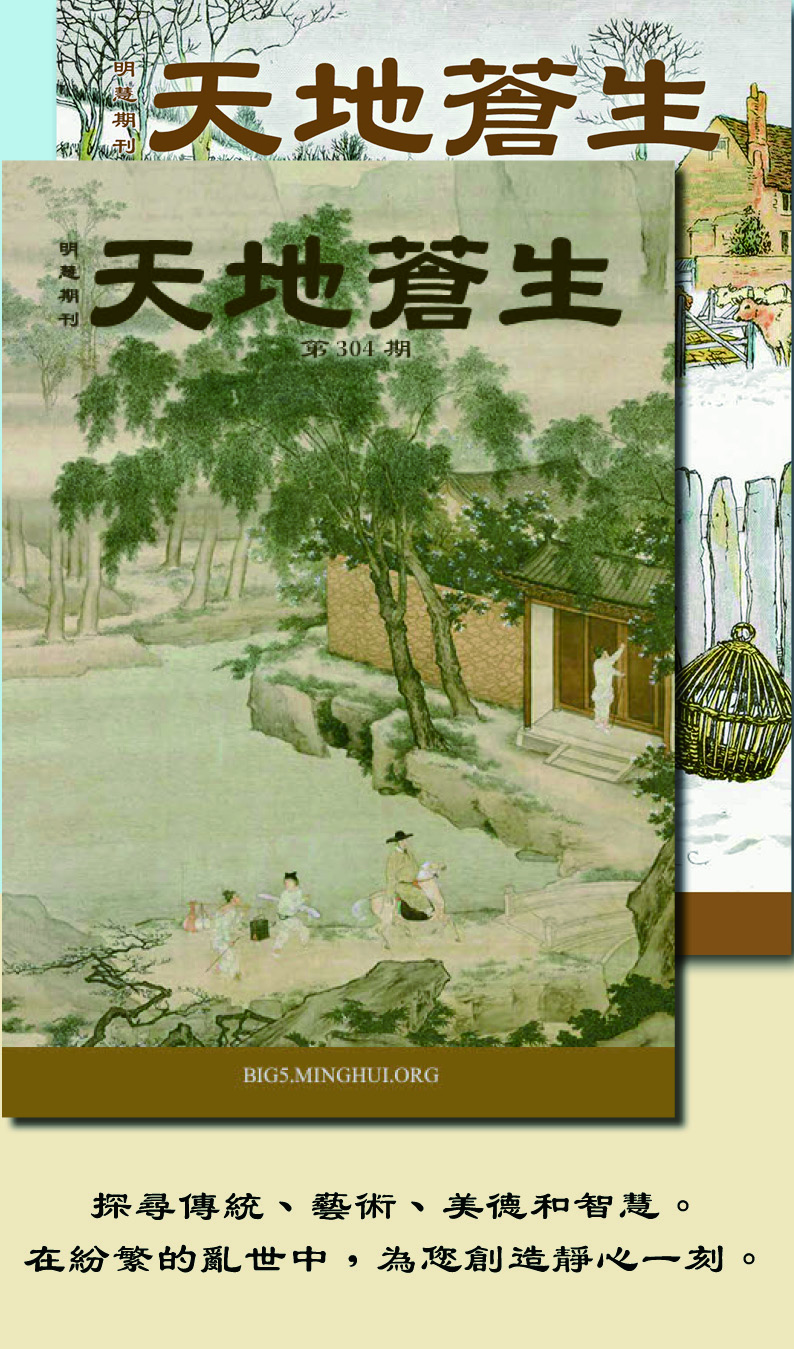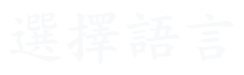二十二个月非法关押中坚定正信,冲破邪恶安排堂堂正正走出劳教所
99年7月邪恶势力在人间的总代表江泽民,利用他手中的强权,开始疯狂地迫害大法与大法弟子,而大法弟子也各自肩负着神圣的使命,开始了护法、正法和救度世人的伟大进程。99年7月23日晚,我踏上去北京上访的列车,但在北京三次被抓,头两次都在驻京办事处跑了出来,再次被抓后被押回老家,在当地拘留所里被非法关押了15天。15天要放人时,要求我写保证书,我不写,单位领导写了保证,并保证24小时监护我。后又于1999年9月28日被抓,并被关进了长春市铁北看守所,38天后被送教养一年,送到长春奋进劳教所,在六大队关押,在2000年7月之前,一直被关押在六大队。
不论是在拘留所,还是在看守所,还是教养所,都有干警不停地做洗脑工作,让写保证等等。我跟他们讲:“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你们管不着,你们现在就是违法的,公安机关以上访为由,讲什么上访扰乱社会秩序,而把大批大法弟子教养,上访明明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却成了扰乱社会,你们执法人员这样解释,这样执法,难道大脑都积水了不成?”干警又讲什么法轮功人员特殊处理。我说:“法轮功学员也是人民大众的一员,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就享受不到公民的待遇呢?对待法轮功这件事有违法的人,正是那些披着人民公仆外衣的各部门执法人员,正是那个强权的操纵者!”在那一年的时间里,这样类似的交谈有无数次,我在这样的对面交谈中,深入地向他们讲法轮大法如何地好,电视、新闻中如何地骗人。
但在2000年7月中旬,暴徒们把长春市几个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到了长春市奋进劳教所来集中洗脑,这真是黑色的7月,暴徒们对大法弟子不择手段的摧残与迫害更加疯狂了,那黑色恐怖造成的巨大压力,使我们从内心到身体都强烈地感受到,这时我们所承受的是常人所无法体会到的。非人摧残的表面上却做出各种假象,他们买来了新的军用被褥,新的脸盆、手巾、牙具,但被褥从未让我们用过,并每天还得把被褥叠得方方正正,白天放在床上,晚上却要放在床下,脸盆和手巾、牙具都从未使用过,都是当市、局的领导来检查时,拿出来摆成整齐的一排,平时反而被收走了。对我们的摧残的目的就是逼迫学员写保证、写决裂、写揭批。
有一次,我们被集中在一起出去走队列,但走的同时逼我们喊口号,极其邪恶、可笑的口号,但70多人喊的声音小得可怜,停下来让四个一排,一排一排地喊,第二排的四个人里面我没有喊,恶警管教沈天鸿问我为什么不喊,我说:“我不喊!”沈天鸿过来连喊带骂,又是拳头又是腿恶狠狠地打我,边骂边问我:“你喊不喊?”本来还有一些紧张和害怕的我,让他一顿拳脚反倒使我的主意识更加清醒了,我大声告诉他:“我不喊,这话我要能喊,我早就被放出去了,我也不可能进来了!”我怒视着他,他也呲牙裂嘴瞪着我,僵持着。我感到一股浩然正气充满胸膛、头顶。这时有一个看管我们的犯人(值班的,是个小偷),看我把管教弄得没面子,从后面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怒视着他,用手指着他的脸大声正告他:“你给我躲远点,我跟干部说话,你给我一边去!”他看我一脸的无所畏惧,退后了好几步。
这时沈天鸿回头又问其他功友:“还有谁不喊?”这时又从队伍中走出三个学员,站在我的身后,剩下的开始训练,但喊的声音小得可怜。回去后个别人说我不忍,太过激,我说:“你们认为喊这口号是对的,为什么声音那么小!?”这是2000年7月中旬的事,当时我们四个在别人都睡了的时候被罚站,后我又在小号中被关了7天,本来罚我10天,但到第7天,恶警居然说我在小号里太享福,加上怕我在小号里炼功,让我回去坐板。
每天坐板从早上5点一直坐到下半夜3点,盘着腿,脸朝前,一动都不许动,动一下就是一顿暴打,还要求我们口里不停地背监规,嗓子都哑了、肿了,但不许停,不停地念。1.8米长的床刚开始坐4个人,后来达到7个人,床上的人数在增加,但人姿势不许变,每增加一个人,大家身上的压力就增加了,已经接近了承受的极限。值班的还不停地说,写保证就上宽管班,爱干啥干啥,看电视说话,洗漱随便,爱吃啥吃啥……。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几个人写了保证倒下去了。其他功友还在坚持着,但这时从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来了四个叛徒,其中有吉林省九台市某小学的校长朱XX,长春东北师大教师单XX,还有一个在某大学当教授的,另一个叫卜X。她们四个来了之后帮助邪恶四处欺骗,来破坏学员的正信与正念。本来男学员正处在承受的极限,她们的无耻谎言正好使有些人找到了逃避的借口,一下子这些人被邪恶击败了。
2000年8月1日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搬三楼,又从别的劳教所转来几个大法弟子,还有几个刚被非法劳教的。新来的有的抗不住恐吓与殴打,写决裂到宽管班去了,能坚定的关在我们严管班。就这样,宽管班已有两个了,而我们严管班只剩一个,摔打中我们剩下了28个坚定的大法弟子。35度的热天,我们被关在屋里坐板,门关死,窗子关死,汗水把衣服全湿透了,门窗玻璃上在往下淌水,就象浴室一样。屋里臭气熏天,因为不允许我们洗漱,屋子里呼吸困难,看着我们的值班在屋里待不了,上走廊上去看着,最后,我们身上生了很多虱子,爬的四处都是,很多功友身上长满了疥疮。这个邪恶的办法是3大队的犯罪队长李长春想出来的,但这28个弟子就是谁也不写什么“保证”、“决裂”,没有玷污大法。
奋进劳教所主抓迫害法轮功的所长叫李健辉,这是个人渣。他指使犯人打骂、体罚法轮功学员,告诉值班的“不老实就收拾收拾”。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他被评为“能手”,现在却已经在竞选中被选下,没能继续当上所长。宽管班的管教潘树强,把邪悟后又清醒的法轮功学员打得脸都变了形,又在他的授意下,值班劳教郭怀成等把大法弟子郑永光打成脾脏碎裂,后脾脏被切除。结果后来潘树强因与所长发生矛盾,被开除,后又因绑架幼童敲诈8万元被抓,真是恶有恶报。而原奋进劳教所所长龙伟锋,曾邪恶地威逼一个学员,当时该学员因承受不住写过决裂,又清醒了,但那时已是全身长疥,痛苦不堪,再次违心地做了一个大法弟子绝对不能做的事,结果被释放了。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大队的大队长尹波以前是集训队队长,吃拿卡要,恶迹累累,收犯人5000、3000、2000、1000不等,给钱多的得分多,好处多,可以不参加劳动,甚至可以任意欺压其他人而不受惩治,给300、500的他都看不上眼。该歹徒在当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的大队长时,对法轮功学员体罚打骂、虐待摧残,
后来歹徒们又以军训为名,对坚定的学员进行摧残迫害。对我们进行军训的是一名当过防暴武警的犯人,我们坚强的毅力,加上我们大法弟子在错误的消极承受中训练特别努力认真,连这个当过武警的犯人都说:“我挺佩服你们法轮功学员。”军训的目的当然是要摧残我们,所以每当所长李健辉一去,如看到犯人对我们不打、不骂,或是打骂不够疯狂,他就大骂对我们军训的犯人,这时这个犯人就用腿狠狠踢我们,用拳头打我们,还大声地骂各种脏话。
摧残在升级。有一天,这个犯人心情不好,说要在训练时收拾我们,训练走正步,累得都已经抬不起腿了,还要马上停下来做150个站起下蹲,做完后连站立都已经费劲了,又马上站军姿,一条腿站立另一条腿抬起挺直,可站了10分钟都抽筋了,站不住就挨打,28个人都挨了打,我的腿也抽筋了,站不住,他过来先是一顿电棍,飞脚踢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我说:“不训练了。”他又过来打我,我便问他:“是谁指使你来打我的?”他说:“打你咋地?”打我违法,侵犯人权,也违反所里的规定,他还要动手,我抓住他的胳膊,决定再不允许他动我一下,再不能老老实实地让他随意打骂,并告诉他,我忍让你,慈悲你,决不是怕你,他大叫:“你xx不练找干部去!”我回答:“你不说我还要去找呢!”
我去找干部,告诉他我不再参加军训,并把被打被骂被摧残的经过跟他讲了,他却说我多事。他打人骂人就合理吗?我让他对我摧残就对了吗?我说:“如果正常军训我参加,你可以问,我军训是训练最好的一个,坐板时,唯一能四个小时一动不动的就是我,但你摧残我们,我就不参加!”
后来,回去后,干部罚我面壁,我说:“我是受害者,向你干警反映,你反倒让我面壁。”他说:“你不炼法轮功吗?你不讲忍吗?”当时我站在中间,两边是严管班的功友,干警指着我,幸灾乐祸地说:“你问问你功友,他们都说你错了。”他问功友们是不是我错了,结果功友们真的回答:“是。”我当时伤心透了,因为这28个人是我志同道合的患难兄弟,他们说今天的事我不忍,与人争斗,我说:“他们随便打我们,他不但违反人间法律,而且他在打大法弟子--未来的神,他的罪业有多重!是纵容他,还是抵制他?!”我指着干警钟文革说:“钟管教,你们穿一身警察衣服,但今天这件事后,我要重新审视你。打人连所规所纪都不允许,而你知道后不加制止,反倒罚我站,惩罚的不是害人的,反倒惩罚受害的,你的良心何在?!这样的所谓军训我决不会再参加!”后来钟文革又单独找我说:“你不参加集体训练,自己单独训,我就给你两科目,一个是正步走,一个是跑步,走一步,你说累了,你就休息。”这是2000年9月的事情。
歹徒们不但在肉体上摧残我们,还在精神上摧残我们,强迫我们念谩骂大法与师父的书,我们严管班没有人念,其他犯人就念,逼我们听;功友因不听他们念,被他们用手铐铐住,把两根电棍夹在脖子两边,嘴里又被插进一根电棍,把他电得整个脸肿得变了样,最后脸上全是硬痂,一块一块很厚的痂皮落下来,嘴唇肿得老高,根本看不出是他本人模样。后来我把邪书悄悄地扔进了垃圾桶,但歹徒们又拿来很多邪书。还不允许我们严管班接见亲人。从2000年8月到2001年5月1日,这么长的时间不让我接见亲人,冬天穿的衣服都是别人给的。在这之前,让接见也是为了让亲属施加压力,帮助他们做洗脑工作。接见时,家属们拿的好吃的很多,回来后我们之间不分彼此,共同享用。但有一次值班人员拿我们的水果洗了一脸盆,要给干部送去,当时我就跟这个值班的人说:“宋庆库,你拿我的东西应该打声招呼!经我的允许再动,你拿我的东西给干部送去,干部领人情领你的情,我们要愿意给我们会自己给,这样的事以后不允许再出现!我这次和你当面说,跟你本人当面解决,这次我不把它捅到局里、所里,以后不发生就完了。”因为我们28个人在一起,有的功友说我小气,斤斤计较,我说不是小气,并把有的功友把钱偷偷地给值班的这件事说了出来,我说:“你为什么给他呢?如果他不是值班的,你会给他吗?如果他对你不构成威胁你会给他吗?是真正的善吗?还是要求得什么,是不是自己有怕心?”这也是2000年9月的事。
在10月1日国庆时,平时不让看电视,那天让看国庆庆典。因平时不让说话,我们就利用这时间,悄悄地探讨着这些天所发生的事,并都认识到不能一味纵容、承受。后来又出现让我们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我们集体反对,并成功。这件小事,使我们认识到意见一致力量的强大,并信心倍增。后来又让我们一天不停地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要大声不停地唱,遭到我们28人的一致反对。大家逐渐学会了拒绝、抵制,树立了信心,从白色恐怖消极承受的阴影中一点点地走了出来。
在2000年10月7日,从严管班中又分出11个人成立了一个班,成了严管中的严管。在坐板时,有个功友轻动了一下,值班的上来就把他的牙打出血了,我们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11个人同时制止、谴责他,他上来就把我从坐板的铺上拉了下来,并扬言要打我,这时,所长李健辉来了,我说:“李所长,你来的正好,我向你反映值班人员殴打法轮功学员……”我话还没有说完,他就手指着我的鼻子,大喊:“闭嘴,你给我上去坐着!”我毫不示弱,也大声说:“我向你反映情况,你还让我闭嘴,我就不闭嘴,我就不上去坐着!”11个人全不坐了,都站在地上,李健辉大喊:“把他给我拉出去!把他给我拉出去!”我也手指他的鼻子说:“李所长,我就不服你,你处事不公,我向你反映情况,你不但不管,还来处理我,你知道为什么值班人员敢随便打骂虐待我们吗,就是你一手指使,你就曾经说过不老实就收拾收拾。”他不承认,我说:“这值班的在这,就他说的。”值班的当然不敢承认,我说:“你不承认,但我们30来人都听到了,你不承认也不行。”李健辉又叫喊:“把他给我拉出去!”我被又拉又推弄进了一楼的小号里,但功友们不知我被送到哪里去了,看不到我回来,他们就集体绝食,也不上板了,这是我后来听说的。每当有干部或领导或犯人来时,我就说关小号的经过,是反映打人的经过却被关了小号。自此,再也没有让我回到大队。自从我被单独分出来之后,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又发生了很多轰轰烈烈的事,为了卫护师父和大法,大法弟子写下了壮美的诗篇。直到2001年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解体。其他功友都被转到了朝阳沟和苇子沟劳教所,而奋进劳教所只剩我们7个法轮功学员。
在小号没几天,又有一个功友被关小号,叫绍维辛,关在另一个小号里。那些违心妥协的人的保证书都贴在走廊的墙上,贴了一片。后来那些人看到我们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班的大法学员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知道做错了,而且有的人做梦梦到天上有一个很大的“李”字,“李”字下面是一竖行一竖行的人名,但被非法关押在严管班的大法学员名字都在每行的排头,他们意识到这是在点化他们严管班的大法学员做的是对的。所以墙上的保证书就有人偷偷地自己撤下来了,但还有很多。那天早晨,绍维辛手臂一抡,哗啦啦地全扯了下来,结果被打了一顿,被扔到小号里。我问他队里的情况,他说全绝食了,误入歧途的大法学员全清醒了。
邪恶被震撼了,集体绝食的被强行灌食,老绍已经9天没吃东西了。看着他那瘦得成了一条的脸,又苍老、又疲倦,说话声音疲惫无力,我哭了。这些大法弟子,他们在社会中都是精英,28个人中有十几个大学生,三个硕士生,只有一个小学学历的,剩下的也都是中专和高中学历,而且在社会上都有着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些善良的人,现在却受着非人的摧残,只因他们坚定修炼大法。在电视新闻中说对法轮功学员如何的好,那是对待已经背叛大法的人的态度,而暴徒们对待坚持真理、坚修大法的同修则是残酷的折磨和恐怖阴影。
在小号的第十天,所里开所谓的批判大会,对坚定的加期,绝食的加期。我们在小号中的也被带出去参加。主席台上坐了好多局、处、所各级领导,会场中央坐着法轮功学员,两边是百十来名手持电棍、手铐的警察,气氛非常紧张,一片恐怖,鸦雀无声。会场前面几个大字写着邪恶的大字,我看着心里就不舒服,这个会我要让他开不成,我要鼓励所有的功友站起来,但我又想怎么能做的更好。李健辉主持会议,刚要大放厥词,这时老绍站起来说:“我不参加这个会!”,但瘦瘦的他声音很小,我就势抡圆了胳膊拍案而起,大喊一声:“我也不参加!”铿锵有力的话语使会场炸了窝,警察拿着电棍向我们两个冲过来,嘴里嚷着“干什么,干什么?”冰凉的手铐打在我的脸上,无数的拳头电棍和飞脚,雨点般地落下,我终于被他们反挎着双手,连打带踢,连拖带拉地被拖出了会场。在会场外,把我打倒,用脚踩着我的脖子,几条电棍同时在身上最敏感的部位又捅又电,捅出了长长的血口子,我把痛苦的叫声用尽全力发出去,我是要告诉会场里的功友,你们志同道合,同甘共苦的功友正在受迫害,你们都站出来、走出来。师父说:“你看到杀人放火那要不管就是心性问题”。现在你们的功友在你们面前受摧残,你管不管!所里二楼、三楼的走廊里站满了女干警,看着他们折磨我,直到后来我身体被折磨得不自主地一抽一抽的,他们才停手,鞋也被打飞了,衣服也被打开了。老绍这时也被打得惨不忍睹,但一声没吭,还有一个功友王辉也走了出来,我们三人被关进了小号,每人一号,都被脚尖离地吊了起来。
散会后,管理科的两个科长与五个干事,还有集训队队长曹岩,把我的衣服脱光,下身因有疥,没脱,我被暴徒用电棍长时间的摧残,他们电我时,呲着牙,裂着嘴,如同恶鬼一般。把我打倒后,用5、6个电棍同时电我,还不停骂着:“看你还炼不炼!”我当时声音颤抖着说:“这么好的法,我怎能不炼!”“我叫你炼!我叫你炼!”他们就象疯了一样,我说:“你们一点人性都没有,我与你无冤无仇,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后来就说不出话来了。这次被电后,心脏时时一阵阵“突突”“突突”,另两个功友也同样被电得没了人样。
第二天早晨在早八点管教上班时,我与功友王辉,在小号中打坐、炼功,这时又象炸了窝一样,劳教们大呼小叫,管教又来了,又把我们狠狠地电了一次,拖回来后在小号里吊起来吊了两天一宿,不给吃不给喝。在小号里我呆了20多天,之后被调到4队,因在小号里被打时手指挫伤,不敢拿东西,去4队后马上让参加劳动,我跟4队队长肖国臣反映个人困难,陈述手伤困难,应该暂缓参加劳动。他竟逼我参加劳动,不参加,就把我打得满脸是血,又让其他劳教按着用两个电棍同时电我,之后心脏更加“突突”很多天。还问我干不干,我索性告诉他们:“就不干!”又要折磨我。管理科又来人了,我跟管理科韩科长、宋科长说:“你们把我的手打伤了,我个人参加劳动有困难,向队长反映,反倒被打!”管理科长威胁我说今天不让你干,明天必须干,不干就收拾你,然后抬脚走了。后经所里决定要把我安排在集训队,此后一直被关在在集训队。集训队的大队长曹岩,也是吃拿卡要,收受劳教人员钱财,给他钱的都成了他的关系户,可以打人、赌博、喝酒等等而无人去管。集训队的恶警马海红,酒后殴打体罚,他曾把我的头夹在腋下,让劳教杨圣军等疯狂击打,打得脸都变了形,满脸满地是血。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大队中有很多学员被分到其他大队,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事情时有发生。
我最初被定为从99年9月28日到2000年9月27日劳教一年,后来被多次加期,成了超期关押。第一次加期3月,第二次又被加期3月,到期后还不放人,我多次找队长、处长、局长,答复是上级命令,不让放人,我跟他们讲理,讲怎么他们违法,他们没理,讲不过我,以后就全躲着我。上访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上访后就被判刑、教养,教养到期还不放,教养期间又受到非人虐待,享受不到公民权利,连劳教的小偷、流氓他们有的权利我们法轮功学员都享受不到。到期不放,我就不停地找各级领导,后来所、处全躲着我,后来又让我参加劳动、“写作业”,写什么改造规划,我都不干,我告诉他们:“我已超期,你把我当劳教,我不把自己当劳教,劳动我不参加,其他劳教参加劳动有奖分,奖分就能早放一天,我劳动积极肯干,但每月都被加期,我参加劳动你加我期,不劳动还是加我期,这半年又到期了,又加70天,70天又到了又加一个月,这一个月又到了还加一个月,教养条例规定加期不允许加过全期的一半,加到半年就违法,可还在不停地给我加。”我拒绝他们的指派和命令,2001年1月到2001年7月16日,这中间又有很多事情发生,但我的环境却越来越宽松,其他队的功友都被两个人夹着走,我不允许他们随便碰我,后来就不再管我了。
在2001年7月16日,我终于从长春奋进劳教所走了出来。当日是劳教所集训队接见日,上午9点30分,两个犯人押着我去接见,我在前面走,到接见室处,我没有停留,径直朝劳教所大门走去,前楼与后楼通道长150米,我凭着坚定的正念,走过迷宫一样的通道,闯过了七道铁门走了出来。劳教所怕担责任,在我跑后,长春奋进劳教所周所长与管理科韩科长开车把《解除教养通知书》送到了我父母手中,并告诉我家人不要说是我自己跑出来的,并跟当地公安局说:“你们的担子重了!”现在当地公安局正四处抓我。
走出来这件事我觉得意义重大,师父不承认邪恶的种种安排,走出来,正是打破了邪恶的安排,正是蔑视、傲视了邪恶,对邪恶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们告诉说是“别说是跑出来的”,我知道这正是邪恶所害怕的,怕大法弟子都打破他们邪恶的安排,他越怕,我越要给它们曝光!
这次能走出来,和功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走出来之前的几次接见对我帮助很大,功友们告诉我邪恶的安排师父是不承认的,要我想办法出来。她们每天都在发正念清除邪恶,让所里无条件释放我,并带家属去劳教所要人,她们做的非常好,即使要人不成功,也使劳教所不敢任意摧残大法弟子,有所收敛,同时在教养所里面的功友,自己也要努力冲破邪恶的安排,齐发正念,共同提高,必然会成功。
我出来后才知道,自从2000年10月我与其他同修隔离之后,我们28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远明的同修被暴徒虐杀,但劳教所死死保密,不敢让世人知道真相。英灵已去,我们留在世间的应当更加努力做好。
在将近两年的关押中,学法是非常不够的。出来马上投入到正法的洪流中来,想做好不出差错,唯有多学法和看大法网站上的文章,才能尽快赶上。在这两年中所做的很多事都有那么多的不足,今后一定在多学法的基础上,在正法工作中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