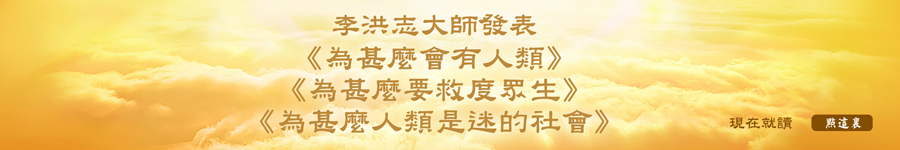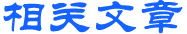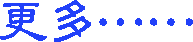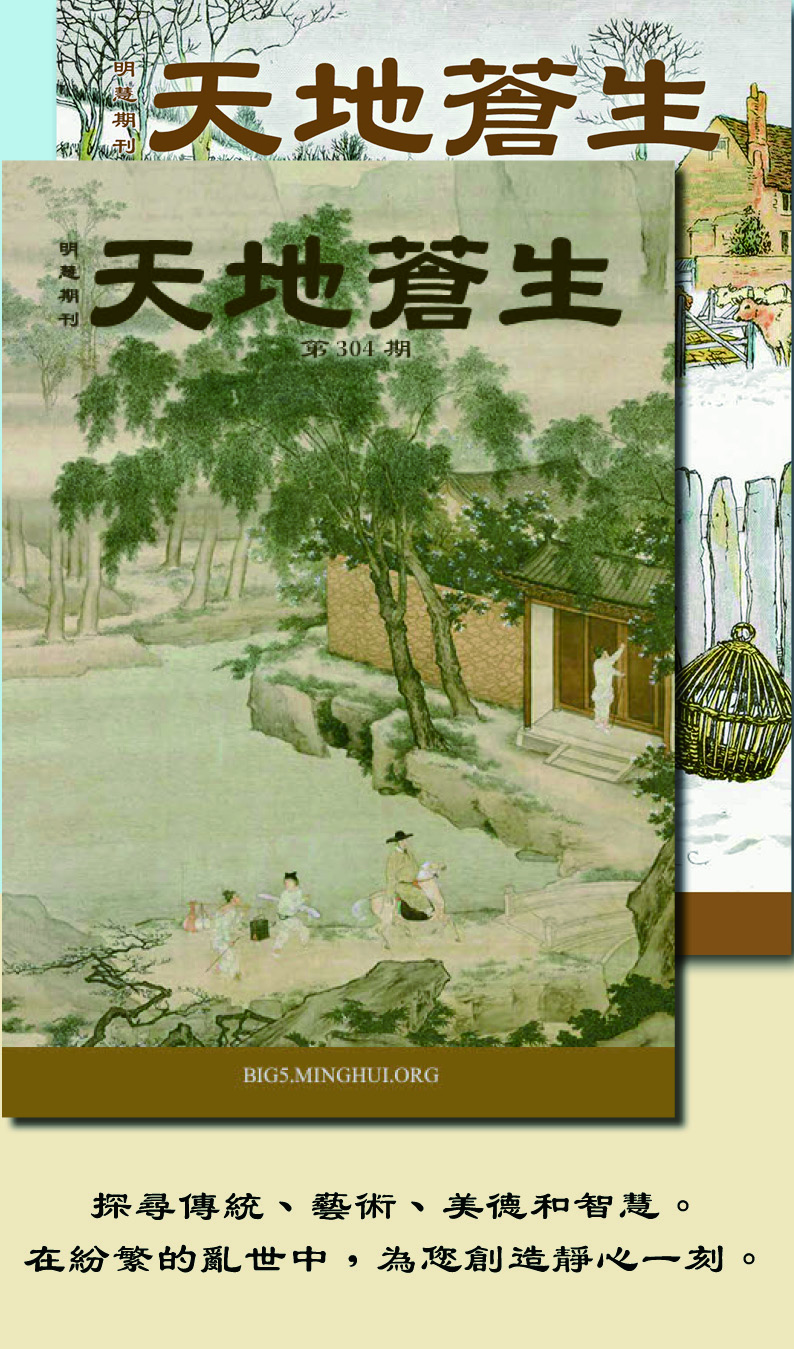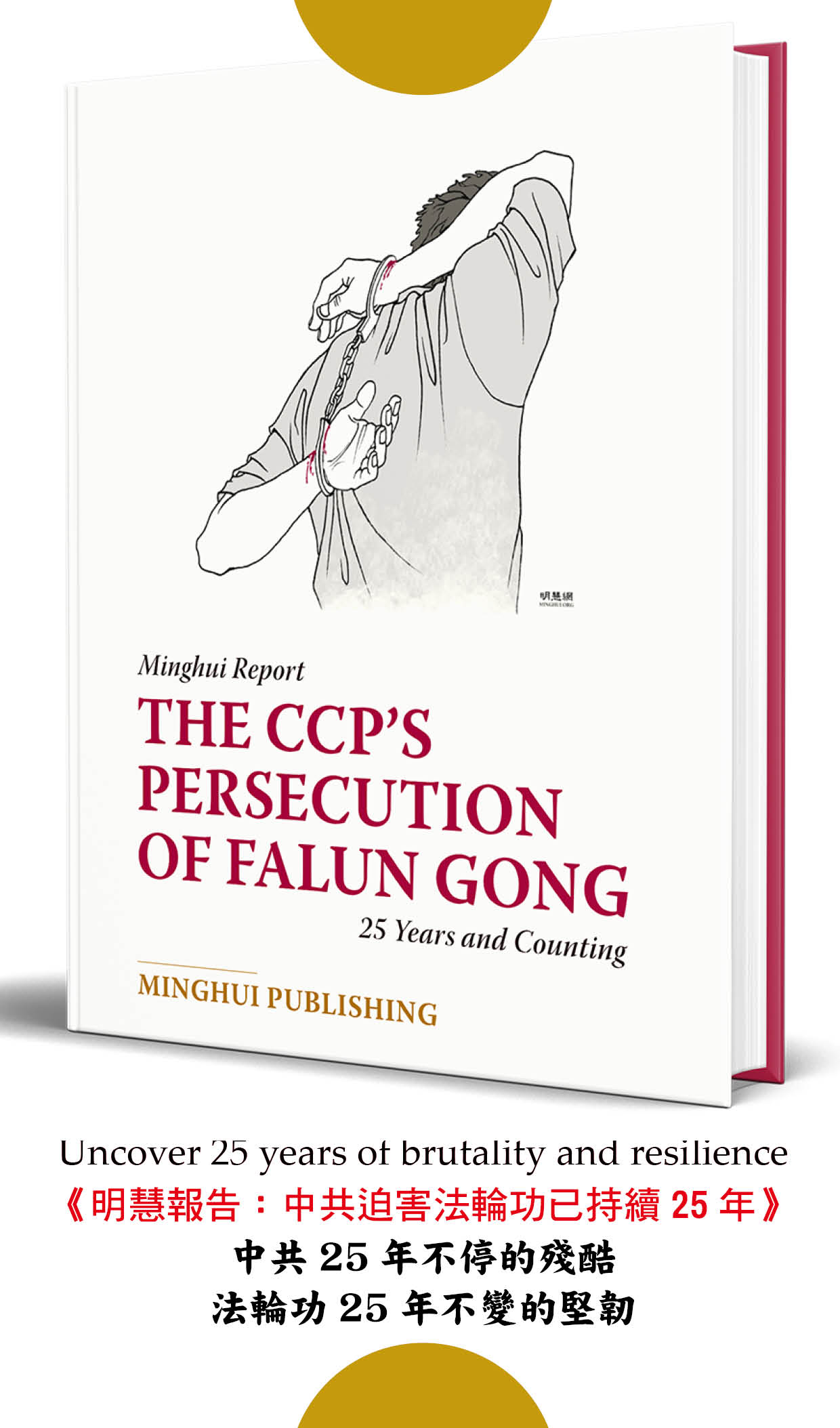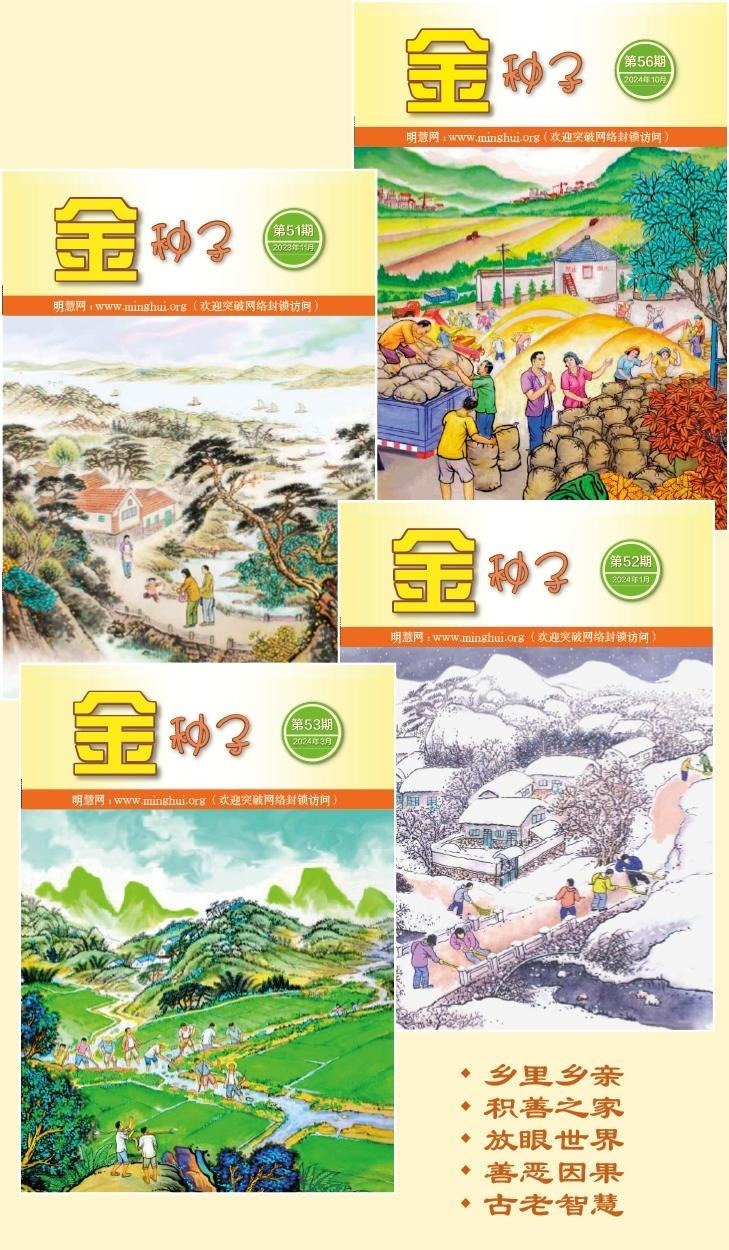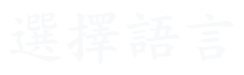我在监狱和精神病院遭受的摧残
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一夥利用手中权力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开始了全面的暴力迫害。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在中华大地上做好人也要受到迫害。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当师父遭到诽谤时,当大法遭到迫害时,为了讲清真相,在人大会议期间唤醒当权者,我于99年10月22日,踏上了进京上访之路。进京后,我看到全国各地成百上千的大法学员来京上访。他们有的因经济条件差从新疆步行进京上访,脚上打泡流水,身上背着七、八双磨破的鞋;有的从四川,全家老少四口(老太太、儿子、儿媳抱着2~3个月的婴儿)也来上访。我被他们护法的一片赤诚之心深深感动。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很多不足之处,并更加坚定了我坚修大法的信心。当晚我们在一起学法交流,决定在人大会议结束之前用我们的亲身修炼的真实感受去唤醒代表们对法轮功所面临无理迫害的关注。
人大会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信访办上访。人大会议期间,天安门广场及其附近大街小巷戒备森严,到处是警车和警察。见外地人或过路的都要问是不是炼法轮功的。回答是就抓上警车,说不是就叫你骂李老师,不骂也被抓走。我们一行人为了顺利到达信访办,就打了一辆出租车避开查问。司机说不敢拉我们直接去那里,那里戒备森严,发现拉法轮功的司机要扣证,只能送我们去离天安门比较远一点的一条大街,叫我们自己往前走。我们下车往前走不远,就有警察追上来问我们是不是炼法轮功的。我们回答“是”,就被他们截上了警车,送到一个警察大院。院内非法关押了不少大法学员,全并排站在院内。大家共同高声背师父的经文与《洪吟》。恶警们还从办公室的窗户内向我们头上扔烟头、泼凉水。
等到院内装满了,我们又被大客车一车一车地送到很远的体育场。数以千计的同修都排站在广场上,一个一个地被恶警审讯。当问到我时,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大法弟子,问我从哪里来的?我也不把地址告诉他。我不报姓名地址,恶警很生气,连打带骂地把我排到没报姓名的队伍里。同修们集中在广场上,整整一天没吃没喝,不让上厕所,不让讲话。他们审了一天没结果,晚上8点多钟,把我们每两个人铐在一副手铐上,推上大客车送到远离北京的延庆监狱。快深夜了,经非法审讯拍照后,送进牢房。
第二天中午,我们配合其他几个牢房的同修,一起集体绝食,抗议这种对大法弟子的非法抓押,要求无条件释放。白天我们集体背经文和《洪吟》,邪恶管教就打我们,罚我们长时间下跪。女管教更是残忍,她们逼我们念墙上的犯人守则,我们不念就没完没了照脸上打。还有的拿我们学员当球踢,踢得弟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直到她们踢累了为止。晚上还一个一个地铐上手铐进行提审。当审讯我时,问我为什么不吃饭?我说这是抗议。问为什么不报名?我说我没犯法,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戴上手铐审我?我不就是上访吗?上访是每个公民的权利,在不公正的情况下允许上访,要不国家设信访办干什么?他们说这是“国家”定的,就得执行。我说“国家”就不做错事了吗?“文革”时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国家”打倒的,怎么平反了?他们理亏,就罚我半站。两手向前伸直,站不住就打,后又罚半蹲,蹲不好也打。有时从早上八、九点带去审讯,到下午四、五点才回来。中午管教睡觉,而我们学员在那里受罚,有的学员蹲下去后,小腿肚上还要夹上一根长棍;有的蹲在小板凳上,时间长了一头栽下去就昏迷不醒,她们就拿针扎她人中。晚上邪恶管教不让我们睡。初冬比较冷,我们就坐在一起盖上被子。半夜我们再悄悄躺下。有时邪恶的管教会突然闯进来把我们踢骂一通,把被子扔到一边去,丝毫没有一点人性。
绝食5天后,他们开始强行灌食。他们依仗男犯的帮助,把我们学员轮着绑到椅子上后,由一名男犯抓住倒背的双手,另一男犯抓住学员的头发往后仰,面部朝上,第三名男犯蹲下抓住学员的双脚,第四名男犯拿钳子把学员的嘴撬开,用钳子隔住上下牙,这样再由狱医拿管子从嘴里往胃里下管,灌一些苞米面稀饭和盐水。有的人被灌得太多从嘴里返上来搞得满身都是很恶心,有的人被灌完之后拖出的皮管的头上都带血。当时那种情景,令看到的人都毛骨悚然,惨不忍睹。想到师父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想到密勒日巴佛和耶稣所忍受的痛苦,我决心绝食到底,不会因为灌食屈服。就这样我们白天被灌食折磨、体罚,晚上管教睡了我们就炼功。一旦有人被发现,就被邪恶管教拉到外面冻好几个小时。度日如年的折磨中,坚持下来的大法弟子们决心横下一条心,大不了扔掉这层壳,也决不停止对这种非人虐待的抗议。
我们绝食了11天,已被折腾得没有了人样,当时根本没想过还会活着出去。被灌食的学员不知道被灌进了什么,全部便水、脱水。可能这个监狱怕这十几条人命出问题,就又分批把我们送回了北京的监狱。我和其中四人被投进了同一个监狱(监狱名字已不记得,挂着“先进监狱”的牌子)的犯人牢房,每个牢房一名同修。我们每天都受审,审不出姓名的就交给犯人处置。不报姓名的就叫犯人打;不吃饭,犯人强行往嘴里塞饼干、倒水;大冬天还逼着你每天洗凉水澡;监狱怕我出问题,晚上叫犯人轮流看守到天亮。
犯人认为我给她们添了麻烦,怨声载道。我想我来这里是想起到一个大法弟子的作用,证实大法,让当权者知道,大法是这样的深入人心,让这么多的人愿意为还他的清白而来上访。当时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这样我说了姓名地址,被公安押回了当地派出所。
没想到刚一进门,就看见几位家属早已等候在这里。孩子的一声“妈”,我顿时心酸,强笑了一下,没吱声,从他们的身边走过去进了审讯室。民警问我为什么进京?我说,上访是我的权利。问我还炼不炼了,我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炼。恶警审了一段时间觉得不能说服我,就把我送进一间小屋,又放进了我的几位亲人,他们抢着扑过来,痛哭流涕,埋怨我心狠。弟弟哭着说:“80多岁的老母亲现在医院住院……”听到母亲住院,我泪流满面。忽然想她毕竟年纪太大了,一旦有什么不幸,亲属们会不会怨恨我这个炼功人,怨恨大法呢?我就这样一下被钻了思想的空子。我痛苦地答应不炼功,去医院看母亲,没有过好“情”关。事后心想,千载难逢的机缘不能错过,即使需要承受亲人们不理解的怨恨,我也要坚持修炼大法。这样派出所就把我又送进了拘留所,要扣留15天。实际上我被非法关押了20多天后,在亲属的催促下,我被押回派出所再一次受审。我拒绝写保证,坚持要修炼。他们又用亲属哭哭啼啼劝说那一套和威胁要送我上大西北的手段,我都没有屈服。一直折腾到晚上8点多钟,恶警们说交5000元罚款后放我回家。我没有,亲属给我交上了。
2000年春节,想到大法蒙冤,师父慈悲救度度众生却受诽谤,大法弟子们坚持真理正义却被迫害,我心情万分沉痛。大法弟子们都想春节早上去本市的曾经集体炼过功的大广场转转,在春节之际出来表示给师父拜个年的意思。结果那天早上,广场四周早已布置了很多警车与警察,天空阴惨惨的。我们几个人看见了就绕开往海边走去。几个便衣上前来堵住我们,叫我们往他们围的包围圈里走。我们不去,他们叫我们骂师父,我大声说你们是在造业!后面立即窜上了个便衣,抓住我衣领把我转了好几个圈后摔在地上,然后把我拖了十多米远,扔进了他们的圈里,用警车把我们送往戒毒所,办班洗脑。
每天来不少“帮教团”成员骚扰我们,我们就向他们洪法。告诉他们我们在按“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做一个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好人有什么不好,还要叫我们往哪里转?难道转到坏人堆里去?还象过去那样自私自利,百病上身?这里不让炼功,还上下搜身,没收了我们自带的大法书。我们集体绝食要求还书,并严厉告诫他们不要太猖狂,善恶必有报。刚绝食两天,他们就来强行灌食。
一天单位来了几个人,说接我走。我觉得车开的方向不对,就问上哪去。他们说溜一圈,一直开到一个部队医院叫我下车。我说你们上医院好了,叫我下车做什么?他们说我们上医院还带上你干什么。叫我上二楼的办公室。他们在里面不知商量些什么,过了很长时间一个部队领导把我叫到一个会议室和我谈话。他问我为什么要炼功?我说我那时身体不好,生活自理困难,各大医院治不了,才去炼功试试。现在我百病全无,一身轻,有什么不好?他说国家不让炼为什么还炼?我说国家做错了。不是允许信仰自由吗?再说要是对我们没好处,能有那么多人炼吗?他说炼功死了好多人,我说那是造谣,你看我怎么没死?炼功要重德,要按照“真善忍”高标准要求自己才能好病。不重德,伸伸腿,抻抻腰就想好病,能说他是炼功人吗?医院天天给人打吊瓶,也天天往外抬死人,你能说是医院给打吊瓶打死的吗?他还谈了7.20的事情。我说那是公安非法抓了我们炼功人。今天能非法抓他们,明天不就可以非法抓我们吗?我们怎能不去讲理要人呢?我头脑清醒,对答如流。之后他出去和单位的人商量了什么。我预感他们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就很气愤地拿上衣服包向楼下走去。走到门口,他们上来5、6个大男人不让我走。我生气地喊:“你们为什么骗我到这里来?你们太卑鄙了!”我死死抓住铁门不放手,他们就5、6个人死命拖我。我已绝食多日,也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使劲大喊“你们太卑鄙了”,想引起人们注意,来看清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僵持了一段时间,他们还是把我拖进了精神病科,拖上了三楼,强行给我换上医院的衣服。我大喊“我没有病”,护士强行给我打针,我一会就迷糊过去了,但隐隐约约地有一点知觉,知道我在被迫害,眼前也出现了幻觉。等到药劲刚一过,清醒一点,我才发现自己的嘴已经发硬,不听使唤,想说话都说不清了。这时又送来了药,强行灌下。就这样我开始整天处在昏迷之中了。开饭了,来人叫我吃饭,我两腿无力,勉强走到食堂,就歪倒在地上。护理们只好把我送回,叫我在床上吃。我的手不听使唤,夹不上菜,人也很迷糊,只好不吃躺下。我努力控制那还有一丝清醒的神经,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炼功人。我就这样每天早晚各一针,灌两次药,整天在床上昏迷、幻觉。
折磨一周后,我被调到大房间。这里不打针了,一天两次药。整天四肢无力、头晕、恶心。在这里每天早上值班主任要查房。主任问我怎么样,还炼不炼功了,跟不跟着瞎胡闹了,为什么不听国家决定。我说我没瞎胡闹,当权者代表不了国家,它们为了一己私利在犯罪。他说:“你现在怎么想的,有没有认为来这里是迫害你?”我没思想准备,不知他什么目的,就没正面回答,只说:“还没想。”他说:“好,你好好想想吧。”就这样由每次3片药加到5片药。第二天我又是如实回答,结果又加了几片药。就这样药片不断地加到了一小把,比别人的多了三倍,同时每周五还单独叫到药房里面再额外吃两个大黄药片并张嘴检查。
以后,从小房间又调来一位同修。她说自己是党员,是单位的劳模。因坚持炼法轮功而被开除党籍。医院把我们两人当作要犯,名字都写在办公室的黑板上。每天班前会都要交代,注意我俩吃药,要严格检查,不准我们走出三楼那道门,除了家属,不准外人探视。由于我的药量不断增加,头昏、恶心越来越重。当我悟到原因后,决定找主任洪法,争取减药。在办公室里,我诚恳地向主任讲,我为什么炼功,如何重德做好人,媒体宣传的是谣言,是把“文革”中的悲剧重演。最后要求给我减少药量。主任答应只能少减两片,说一下减多对我不好。
来到精神病病房,虽然没有监狱的那种直接的暴力摧残,但是精神上的折磨并不亚于直接暴力对肉体的折磨程度。由于长期服用大量的药物,全身水肿。脸肿的泡泡的,脸色很难看。凡是来看我的人都说我变形了。在这里得不到学法炼功,还要和一些疯子搅在一起,整天她们大喊大叫,手舞足蹈,搞得我心神不定。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每天还逼着我们到礼堂和男女疯子们一块娱乐。有时看到一些丑恶的动作,真是令人作呕。这么肮脏的地方,任何正常人生活在这里都会痛苦不堪。有一次我突然思想上象要崩溃了一样,好象要给逼疯了似的。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心里想,不能疯,千万不能疯在这里!我有法在,有师在,不用怕,就这样使劲往下压。心中不断地念着《洪吟》中的《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惧十分。”念经文《位置》“……一个修炼人所经历的考验是常人所无法承受的……”,念:“坚修大法心不动……”等等,终于克制住这股往上乱翻的念头,使心情恢复了平静。
难熬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病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据同修的单位来人讲,如果我们不放弃修炼就要长期呆在这里。可能我们的正气感化了医院的常人,都知道了我们是好人,连主任也催促单位尽快把我们接回去。在主任的催促下,终于结束了三个多月的折磨,我被接回家了。临走时,我向主任告别,他一直目送我走出大门,从他的表情上,我深深地理解了他那种歉意。
好几个月的强行用药把我折磨成了一个病人。回家后我把医院开的药全扔了。我两眼红肿,从里到外糜烂,睁眼都困难。不久以后,耳朵也里外流脓,脖子也出黄水。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由于我坚持学法炼功,症状一天天地减轻,身体又一天天的好起来。我下定决心,生命不息,炼功不止。任何残酷的折磨都改变不了我修炼的心。
在江泽民集团的血腥迫害下,到目前为止,追求“真善忍”的大法弟子已经有近300多名迫害致死,500多人被非法判刑,1000多人被非法关进精神病院强行治疗,120000多人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劳教所受着毫无人性的折磨!我就是其中一个被迫害者。我强烈抗议江氏政权对大法弟子所实行的惨无人道的酷刑!善良的人们!我愿用亲身的经历呼唤你们对正义的良知,希望在真相面前拨开迷雾,看清江氏政权的邪恶面目,并真正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
(英文版:https://www.clearwisdom.net/emh/articles/2002/1/7/17481.html)
English Version: https://en.minghui.org/html/articles/2002/1/7/17481.html